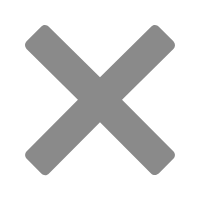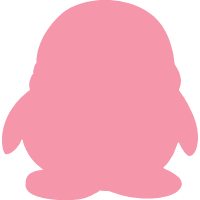第一百一十章 偷偷的哭
“晨心别闹,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快说吧。”我重新坐回了椅子上说道。
“就是这个事啊,你能答应我吗?”夏晨心道。
“不是,你为什么让我去追求你姐姐啊?”
“姐姐她其实挺可怜的,之前本来都快订婚了,但是因为我的原因结果没能订成,那个男人和另外的女人好了。”夏晨心情绪有点低落的说道。
“该不会是你把你姐和那个差点成你姐夫的人给搅合了吧?”我猜测道。
“不是,我哪有那么厉害?还是因为我这个病的原因。”夏晨心摇了摇头道。
“你的病?虽说治疗起来不是很容易,但是以你们家的经济完全不是问题啊?不能因为这个就嫌弃了吧?”
“你别急,听我慢慢跟你说。”夏晨心顿了顿说道:“记得小时候我们相见时那个奇异的场景吧?那是我开始被发现心衰的时候,当时身边没有人,我以为我要死掉了,结果后来是我姐发现了我,及时把我送到了医院,确诊为左心衰,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虽然一直在治疗,但是还是在慢慢恶化。”
“我爸找了很多医生,但是都只是延缓了病情,一直没有被根治,以现在的条件对我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被根治,发展到全心衰之后唯一的办法就是心脏移植手术。而心脏是人体不可或缺的器官之一,又怎么可能有人会轻易捐献?我爸也知道这个问题,所以在医生说出这个方案之后爸爸他就四处找人找关系,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好心人的捐助,只可惜一直都没有合适的出现。”
“随着我的病情加重,爸爸也越来越着急,从正规途径获取不到,最后看上了黑市,在里面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成功找到了一颗能够匹配的心,爸爸他很开心,可是在交易的时候出了意外,这个组织早就被警察发现了,一直在准备抓捕,而爸爸前去交易那次就正好碰到抓捕的时候,爸爸作为非法买家也被一起抓走了,现在公司就只有姐姐一个人在顶着……”夏晨心说着说着便开始抽噎起来。
按照夏晨心所说所有事情的起因确实都是因为她的病引起的,但是最终却不能去怪罪她,患上这样的病也不是她所愿意的,所以没有任何可以强加给她的指责,可她依旧把左右的责任都归咎在自己身上。
从包里掏出来一支烟想点上,又想起这是医院,而且夏晨心的情况也闻不得烟味,又重新把它塞回了烟盒里。对于夏晨心爸爸的做法我也没有办法去评价,或者说是没有资格,站在夏新雪这边,他是一个好爸爸,只想帮助女儿治好女儿的病;可是站在那个被摘取器官的人的角度,夏晨心的爸爸又是十恶不赦的歹徒,我没有办法因为夏新雪的关系就站在她爸爸的立场,然后歌颂他是伟大的,也没法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去批判谁,所以整个事件我没有什么资格去评价,因为我没有做过爸爸,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我只能说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性,所有的事情也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他们都是一起存在的,只是看错的一面大还是对的一面大,对这件事我依旧给不出是对是错的答案,如果是有旁观者在,或许会有很多人指责她爸爸丧尽天良,但我也相信会有一部分人能够理智的看待事情,因为他们可能会知道,这种事情如果放在自己身上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爸爸他是被有心人坑了一把,而且对面找关系想要在最后的判决上从严判处,也几乎是在同时,商场上之前一些有合作的公司也纷纷对我们避而远之,他们都知道有人要对我们家出手了,也是在这个时候那个男人离开了姐姐……我好多次醒来都看见姐姐在偷偷的哭……”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我觉得以夏新雪的性格应该不会让她妹妹知道这么多的,但她又是从那儿知道的呢?
“是那个臭男人告诉我的,她喜欢我姐姐不假,但是他就是为利益活着的,当初我们家还好的时候,和我姐姐在一起既得到了自己喜欢的人又能强大家族,可是我们家稍微露出点颓势之后他就毫不留情的跑了。这是我追问他,他念在对姐姐的一点情分上才告诉我的。”
夏晨心顿了顿,又哭又笑的说道:“你说我是不是很可悲?自己的病情,自己的家庭情况都需要一个外人来告诉我了,她们都瞒着我,害怕我,不敢告诉我……”夏晨心说完终于大哭了出来,情绪变得有些激动,呼吸变得困难了,我见状赶紧将旁边的鼻氧管给夏晨心戴上,又帮她打开了氧气,这样能降低一些她呼吸的频率。
看着夏晨心哭的那么厉害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她,但心底却隐隐作痛,为她的遭遇感到痛心。如果她和她的家一切都还好,那她一定会幸福的像个小公主,不,只要她还好,就一定不会过的这么苦,因为现在的她正是十八九岁的大好青春,本应该是青春懵懂快乐活泼的女孩,现在却被困在病房里,好像除了姐姐也没什么朋友来看望她,就连放一次风筝也快变成奢望了,这所有的痛苦源头都在病魔上,如果我是一个心血管科的医生,我必将穷尽一生寻找她这种心衰情况的解决办法,但这些都只停留在如果,我没有学医。
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只能递给她一个肩膀依靠着,轻轻拍着她的背,希望她能好受一点,夜晚才是人最脆弱的时候,说的一点都没错,想想有多少心事都是在夜晚吐露的呢?我也不知道她究竟压抑了多久,但相信这是一次彻底的释放,因为我肩膀已经被她的眼泪打湿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渐渐的没有了哭声,呼吸慢慢变得平缓起来,她靠着我的肩膀睡着了,应该是哭累了。
我小心翼翼的将她的头抬起然后放在枕头上,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着,偶尔还会口齿不清的呓语几句,脸上挂满了泪痕。我将单薄的被子往上提了提,这才重新在陪护椅上坐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