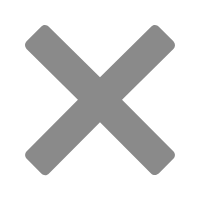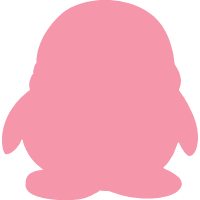-
人皮玩偶的复仇
本书由智阅文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我是林氏一族的第十代孙。
据说,我家祖上曾是整个林城首富,金玉投壶、锦绣铺地,出入皆有奴仆随行。
但这些风光的过去,不过是幼时爷爷说给我听的故事。
自我有记忆起,我们就住在坤隅村,村里几乎没有外姓人。
同时又偏远得很,骑车去镇上少说要一小时。
唯一能证明他的话的,只有几本厚重但枯朽的族谱族志,和祠堂里密密麻麻的牌位。
可这些并不能改变我们穷苦的生活。
我是我们这一代唯一一个考上大学,走出村子的孩子。
也因此成了全村的希望。
为了学业,我已经有三年没回家了。
只是两天前,我收到了四叔公病重的消息。
四叔公看着我长大,供我上学,我不能不回来送他最后一程。
按规矩,今晚该由四堂兄守夜,但他饭后突然发烧。
我成了代替他的人。
「三叔,我出去一趟。」
我压低声音和三叔说话,顺便站起来,给四叔公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三叔的脸隐没在黑暗中,微微点了点头。
我有些奇怪地看了看他,三叔不是这么沉默的性子。
不过生父病重,他心情不好也是应该的。
今日初一,天色昏暗。
我依靠着记忆,向茅厕走去。
但没能找到地方。
难道是推倒重建了?
我正琢磨着,突然听到了沈阿婆的声音。
「林耀,跟我走。」
沈阿婆手里拎着昏黄的灯笼,佝偻着背给我引路。
明明是八月,路上居然带着一丝凉意。
我缩了缩脖子,紧紧盯住烛火摇曳的灯笼,生怕它就这么灭了。
村里的晚上很安静,只有我踩踏在叶子上的沙沙声。
「沈阿婆,还没到吗?」
走了一段路,我有些难为情地问她。
「到了,去吧。」
她应声停下脚步,指向面前黑黢黢的地方,那是一栋矮房。
人有三急,我立刻就向那边冲过去。
却有一道白光在我眼前闪过。
我狼狈伸手抵挡,但依旧忍不住流出眼泪来。
「梁永你干什么?」
眯着眼睛,勉强看清面前的人,我没好气地问。
「我还没问你要干什么,不是在守夜?」
来人面色严肃。
我与梁永也算一起长大,他惯会嬉皮笑脸,我还没见过他这么严肃的样子。
「我出来解个手。」
我揉着眼睛解释。
「解手解到沼泽边上来?」
「什么……」
梁永的手电筒扫过我身侧,硬生生打断了我的反驳。
那里不是我之前看到的茅厕,而是正在冒泡的沼泽。
一阵热风吹过,身后的树林传来声声蝉鸣。
八月的夜晚,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要是一脚踩进沼泽,我怕是会死得渣都不剩。
「我是跟着沈阿婆来的。」
我轻声喃喃。
他用更怪异的眼神看着我。
「林耀,你不会撞鬼了吧?村里哪有姓沈的人家?」
他说的对。
我们村里大多姓林,只有一户姓洪的人家,和梁永这一个姓梁的。
而且,村里人少,每一个我都认识。
几个阿婆虽然上了年纪,却没有一个驼背。
我抬眼,看向之前沈阿婆站的地方。
此刻那里空空荡荡,看不出曾有过人的样子。
而且,我后知后觉地想,虽然村里落后,但也通电好几十年了,哪还有人家留着烛火点的灯笼?
不会真的有鬼吧?
想着小时候听过的鬼故事,我心里一阵接一阵地发慌。
不敢再看身侧的沼泽,我连忙拉过梁永。
「走走走,我们快点回去。」
我快步走回了四叔公家,却发现那里灯火通明。
可能出事了。
心里一个咯噔,我和梁永对视一眼,赶忙往院子里跑。
刚挤进人群,我就看见三婶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问过身边人我们才知道,出事的不是四叔公,而是四堂兄。
三婶起夜,想为发烧的堂兄掖一掖被角,才发现人已经没了呼吸。
「你个杀千刀的,非要儿子跟着守夜,现在满意了?我可怜的儿啊!」
三婶一边抹泪一边骂。
可一门之隔的三叔,却始终没有反应。
她的表情越发气愤,我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走时,三叔还没睡着。
这么近的距离,他不应该听不见。
这种预感在她踹开门时打到了顶峰。
她一掌拍在三叔的背上。
「你个混账玩意儿……」
仿佛被掐住了喉咙,三婶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尚反应不过来发生了什么,只是清楚看见了她表情的变化。
从愤怒到震惊,再到惶恐。
「死、死人啦!」
直到三叔的身体落到地上,发出「咚」的一声,她才尖叫起来。
仿佛一滴水落进沸腾的油锅里,院子里的人炸开了声。
我大着胆子走上前去,碰了碰三叔的身体。
那不是活人温暖而柔软的触感。
他的身体冰冷,摸上去有些僵硬。
三叔真的死了。
看着他弯曲的膝盖,我抖着手碰了碰他的指关节。
没有动。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
我倒退了几步,摸着胸膛大口喘气。
体温散尽、出现尸僵,三叔死了至少有三个小时。
可是现在不过半夜一点,而我们进屋时,都有九点了。
从这里到沼泽,我走得再慢,也最多用上十分钟。
也就是说,在我离开前,三叔就已经死了。
我和死尸在房里待了半个晚上!
而且,我离开的时候,三叔还点头了。
想到这里,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村里的晚风是暖的,我却如坠冰窟。
「医生来了,医生来了。」
年老的村医被村民架着走过来。
他的脸色同样有些白。
「像是内脏出了问题。」
他很快得出了结论。
「应该是内出血,他摔过吗?」
「没有,没有。」
三婶捂着脸摇头。
她突然顿住,像是想到了什么,通红的眼睛望向我。
「他下午去接过小耀了,小耀你来说,他有没有出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