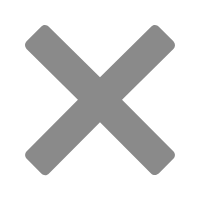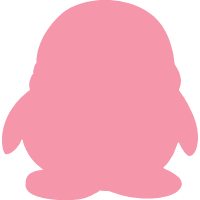-
装成小白花舔了沪圈太子爷三个月
本书由智阅文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01
装成小白花舔了沪圈太子爷三个月,却在他生日那天听见他同他的好兄弟说道。
「陈清清?无趣。」
呵呵,嫌我无趣是吧,老娘还不伺候了!
我摔了他的蛋糕、掀了他的饭桌,脚下八厘米的高跟鞋直接甩在了他脸上。
老登!惹上东北女人你算踢到铁板了!
后来他头上顶着纱布让我对他的伤口负责。
我看了看电视机里正播放的乡村爱情片段:铁锹战神王老七怒扇谢广坤。
欣然点头。
好啊!那就准备好受死吧!
1
闺蜜在酒吧找到我的时候,我正靠在一对男模怀里喝的五迷三道。
「所以你是真的放弃季宴了?」
「不然呢?那个狗男人,留着过年吗?」
我白了他一眼专注喝酒。
我叫陈清清,今年22岁,是沪上陈家的大小姐,但是此前的21年,我都生活在美丽的故乡大东北。
随着我爹和我哥在这边的生意越做越大,我们才举家搬了过来。
第一次见到季宴是在三个月前的酒会上,只一眼我的目光便落在他身上收不回来。
家人们,你们相信一见钟情吗?
反正我是不信,因为我纯属见色起意!
没办法,他实在是长得太合我的胃口,肩宽腰窄大长腿,一张清冷英俊的脸上满是禁欲感。
基本不用打听,我就了解到他是沪圈的太子爷季宴。
于是我开始了自己长达三个月的舔狗生涯。
白天送水送饭送礼物,晚上微信里嘘寒问暖。
打听到他曾经有一个小白花白月光,我当即连学带演,憋着一腔东北口音扮演起了白莲花。
三个月啊,我每天起早贪黑舔他舔的当他妈都能合格。
可就在昨天他的生日宴上,我在包厢门口亲耳听见他对他的兄弟说:
「陈清清?无趣!」
玛达把卡,天地可鉴!为了舔他我勤勤恳恳装了三个月的小白花,他现在竟然嫌我无趣!
叔可忍,婶不可忍!老娘我还不伺候了!
我推门进去,里面的人见我来了瞬间噤声。
倒是季宴的兄弟在一旁开口。
「呦,陈大小姐终于来了,不知道给我们宴哥准备的什么礼物。」
他看不起我,我是知道的,虽然我家的公司如今蒸蒸日上,但他们还是打心眼里瞧不起我这个外来户。
原来为了追季宴,我勉强还忍一忍,但今天,对不起,我忍不了一点!
我将拿来的礼物扔在地上,走到蛋糕旁,伸手猛地一推,几层高的蛋糕直接被掀翻在了地上。
包厢里一阵尖叫,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我靠你疯了吧!」
疯了?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更疯的。
我直接将酒桌整个掀起,满桌的酒菜洒落一地,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先前讽刺我的那人来拦我直接被我一个过肩摔掀倒在地。
忘了告诉他们了,我上学时父母为了防止我被别人欺负,从小就让我学习跆拳道,就刚刚那样的菜鸡,我一个打十个都不在话下。
见我伤了人,一直冷眼旁观着这场闹剧的季宴终于出声:
「陈清清,适可而止。」
他不出声还好,一看见他我就能想起我这三个月当舔狗的委屈,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手边没有趁手的工具,我直接将一双高跟鞋脱下来向他砸去。
他侧身躲过了其中一只,却被另一只直接呼在了上半张脸上。
见季宴被砸中,众人忙围上去查看。
而我此时的火也发的差不多,当即趁着混乱离开了包厢。
2
司机见我光脚出来,连忙让我上车。
直到坐在车里怒火褪去逐渐清醒,我才开始感觉到委屈,眼泪一滴一滴砸在了裙子上。
司机陈叔见我一直哭安慰了一路,一下车我就不顾他阻拦光着脚回到了公寓里。
说起来,这间公寓还是我为了离季宴公司近一点买的,现在要不是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我坚决不会再回到这。
回到卧室,我直接打开衣柜,将满柜子的白色连衣裙通通抱了出来,扔到了门外。
要不是打听到季宴的白月光喜欢纯白色裙子,谁会天天一身白色活像是去奔丧一样啊!
一晚上又是砸场子又是哭,我早就疲惫,直接妆也没卸就倒在床上昏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我是被一阵门铃声吵醒的。
打开门就看见我哥陈澈站在门外。
见到我他吓了一跳。
「我去你什么情况!你是背着我和爸妈整容失败了吗?眼睛肿的跟核桃一样!」
听见他的话我连忙跑到洗手间。
镜子里女人脸上的妆早就花的不成样子,黑色眼线混着眼泪早已干涸在脸上,仅剩的一点口红糊在唇边
眼睛如同陈澈说的肿成了核桃,活脱脱就像个女鬼!
过了几秒,洗手间传出了我的尖锐爆鸣声。
这是哪家的眼线笔和粉底液,我要投诉他!
2
我收拾好从洗手间出来时,我哥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你昨晚不是去给纪宴过生日了吗,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幅鬼样子,听陈叔说还哭了?」
我靠在沙发上一副死鱼状。
「我以后不打算再追他了,我把他的饭局给砸了。」
我哥听见前半段刚打算安慰我,又突然听见了后半段。
安慰的话瞬间卡在了嗓子。
下一秒我哥猛的从沙发上站起来颤抖着手哆哆嗦嗦了半天。
半晌才磕磕绊绊的讲出话来。
「你、你、你说你把他饭局砸了!?」
我哥的话中带着难以置信,下一秒又似乎想到了什么。
「你没打他吧?」
我明显看见我哥的眼里仅剩的最后一丝期待甚至祈求。
「没有。」
我哥松了一口气。
「我给了他一飞鞋,正中脑门。」
我感觉我哥快不行了。
他的眼里带着悲壮、惨痛甚至还有一点同情。
这个我多少能理解,因为他曾经也被我一飞鞋砸过。
那时候他还是个熊孩子,非要抢我玩具,于是我一个飞鞋给他拍的哇哇痛哭,还被我妈训了一顿。
也是从那个时候我发现了自己异于常人的技能,扔别的都不准,扔鞋一砸一个准。
最后我不知道我哥是凭着什么毅力撑着,哆哆嗦嗦走出我的小公寓的。
他只是在离开时告诉我最近别到季宴面前转悠。
倒是正合我意,我巴不得之后再也见不到他。
况且人生也不只有那些舔舔狗狗,姐的生活多彩着呢!
于是夜里我便约了闺蜜夏凝去泡吧,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没关系!这天崖何处无芳草。你何必单恋那季宴一座大冰山啊!」
「放弃了他那一棵歪脖子树,还有一大片森林等着你呢。」
我点点头表示她说的非常正确,手在一旁小狼狗的腹肌上就没离开过。
啧啧啧,手感真好。
之后的几天我没再见过季宴。
倒是听我哥说那晚生日宴被我掀了个底朝天,季宴额头还受了伤,许是被我用高跟鞋砸伤这件事太丢人,他当即就让人封锁了消失,知道实情的也只有当时包厢里的几个人。
第二天开会众人见他额头围着纱布,他还解释是不小心出了个小车祸撞在方向盘上了。
殊不知其实是被我砸的。
我哥说到这还凉凉的瞥了我一眼。
也不知道他付出了什么代价,才让季宴选择息事宁人放过我的。
反正季宴半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找到我报复。
再见到他是半个月后,我早已从小公寓搬回了家里。
此刻正坐在客厅看电视里播放的乡村爱情:铁锹战神王老七怒拍谢广坤。
正看的起劲,管家便招呼我说季宴来了。
我一回头,见他已经走进了客厅。
也不知道他来的目的,我便装作没看见他。
直到他走到电视旁,站在那一动不动的看着我。
我刚开始还能装装样子,可他的目光实在是太有存在感,看得我浑身不适。
我放下手中的果盘擦擦手就打算上楼,路过他身边,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站住。」
「干、干什么?」
我强壮淡定了问了一句,他现在的样子怎么有一种要杀了我的感觉。
「你说呢?半个月前你毁了我的生日宴还将我砸伤。」
他说着,脸色凉的仿佛一块冰块。
「这刚过多久?别告诉我你忘了!」
「你想怎样……」
我说着偷偷在后面抬脚打算给他一拖鞋,可这家伙立马就发现了,将我的两只手都握在了一起。
靠!手大了不起啊!
他冷哼一声:
「你砸伤了我自然要对我负责!」
「虽然我现在头上的伤口已经好了,但心灵上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我要你去我家当一个月的保姆还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