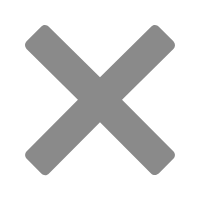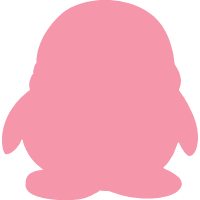-
木偶师
本书由智阅文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我爷爷是十里八乡最有名的木偶师。
他的木偶戏栩栩如生,精彩绝伦。
每次一有人家办喜事,他们都会请上爷爷去演出戏。
这天,我不小心把爷爷最喜欢的木偶的头给弄断了。
当天晚上,爷爷的头也断了。
1
我刚推开门,就看见眼前极为惊骇的一幕。
爷爷的头被提木偶的细线吊着,脖子上勒出暗紫的红痕。
创面口整洁干净,连一丝血沫都没有,仿佛爷爷的身体里根本没有血。
他的头滚落在地,表情狰狞,眼睛还睁着,直直对着我,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
那样子,就像是有人拿着提线从背后勒住爷爷,再用线把脖子切断。
我被吓得一屁股摔倒,手里原本要送给爷爷的饭撒了一地,裤裆一片濡湿,忍不住鬼哭狼嚎起来:
「爹,爹!」
听到我的动静,我爹李海常摇着轮椅,快步走进。
看清屋里的景象时,他一愣,随后重重叹了口气,一言不发。
我紧紧抓住爹的裤腿,六神无主:
「爹,爷爷这是被谁害死了?我们该怎么办?」
「哦对,报警,报警,我这就去镇上报警。」
说着,我从地上爬起,踉踉跄跄地往外走,却被爹一把拦住。
「不用报警,你爷爷寿终正寝,是件喜事。」
我瞪大了眼,看着爷爷还掉在地上的头颅:
「这?寿终正寝?」
「这明明就是被人给害死的呀。」
「到底是谁家看不惯我们,要用这么惨绝人寰的手段来对付我们?!」
爹瞪了我一眼:
「这件事不能伸张,对外就说爷爷寿终正寝,别让其他人知道。」
「还有,我一会儿就开始操持爷爷的后事,你一会儿去通知父老乡亲,晚上把爷爷的葬礼办了。」
我急了,大吼:
「可我们连杀害爷爷的凶手都还没抓到,怎么能给爷爷举办葬礼?!」
话音未落,一个巴掌随之而来。
我捂着火辣辣的脸颊,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人。
他坐在轮椅上,胸膛剧烈喘气:
「老子让你去做就去做,哪来那么多废话?!」
「这件事,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帮不了你的忙,你还是赶紧省点力气,按老子说的去做!」
我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满怀孤勇的心一下子跌落谷底。
好半晌,我才木讷地回了一句:
「好。」
2
当天晚上,爷爷的棺椁就入了灵堂。
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大多是请过爷爷去家里演戏的村民。
他们没有多问,对爷爷寿终正寝的解释似乎也没有任何怀疑。
他们用例行公事一样,和爹说了几句体贴话,又走到爷爷的棺椁前朝他鞠了一躬。
我站在棺椁旁一一回礼,却发现他们看爷爷的眼神都有些复杂。
我悄悄回头,往棺椁里看了一眼。
爷爷的头已经被爹用提线缝了起来,提线透明,再加上脂粉的装饰,基本看不出来爷爷死前的惨状。
此刻的爷爷正躺在棺椁里,闭着眼睛,一副安详的模样。
可我依旧能想起早晨看见爷爷尸体时的惨状。
稀奇古怪的死法,让人心中恶寒。
我突然想起那个被我弄坏的木偶。
我曾意外撞见过,爷爷在屋子里看着那些木偶长吁短叹。
可这和爷爷的死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好不容易送走所有宾客,屋外的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爹沉着脸,挪着轮椅朝我走过来:
「你今晚留下来守灵,明天就安排爷爷火化入土。」
我愣住:「这么急?不能再多留几天吗?」
爹横了我一眼:
「你知道什么?照做就是了。」
我不情不愿地应下。
当天晚上,我穿上麻衣,跪在棺椁一侧,脑子里全是白天那一幕。
突如其来的巴掌,迫不及待地遮掩,似乎浇灭了我和这个男人之间最后一点情分。
我这个所谓的爹,从我记事起就一直不喜欢我。
小时候,一有点什么事,他就对我非打即骂。
竹条,扫帚,拖鞋,哪一样都在我身上挨过。
后来他的腿废了,脾气就更是暴躁古怪,时不时就拿我出气。
那段时间,我根本不能出现在他面前,一旦被他看到,他就又会寻个由头来打我一顿。
我其实一直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
别人都把自家的小孩当宝贝疼,可在我们家,我仿佛就是寄人篱下的扫把星,多看一眼都招人嫌。
而我娘又在生我的时候就难产死了,我从没见过她,只在老照片里见过她模糊的面容。
我没有娘护着,也没有爹疼,就像个没人要的小孩。
好在还有爷爷护着我。
都是因为有爷爷在,我才能安然无恙地活到今天。
可我却连帮他报仇都做不到。
想着想着,我的泪又落了下来。
窗外的月光悄悄洒进屋里,整个灵堂回荡着我呜咽的哭声。
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哭累了,趴在棺椁上睡了过去。
迷迷糊糊间,我似乎看到了爷爷的身影。
他穿着寿衣,动作有些僵硬,正站在不远处呼唤我:
「小六子,小六子。」
我被吓了一跳:「爷爷?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他有些着急,脖子上顶着的脑袋摇摇欲坠:
「是啊,所以我才来给你托梦。」
「接下来我说的话你都听好了,一会儿一记得按我说的去做。」
我有些蒙圈,但还是点了点头。
爷爷满脸严肃:
「你去我房间里,衣柜下边那个装木偶的箱子。」
「你把那套木偶全部拿出来,天亮前把它们烧了。」
「记住,别让任何人知道。」
我丈二和尚摸不到脑袋:
「那套木偶不是我们家祖传的吗?为什么要烧掉啊?」
爷爷急了:
「你别问这么多,你只要按照我的话做就是了。」
「快点,时间来不及了,你快去!」
「等等!」
我赶紧阻拦,可追问的话还没说出口,耳边就传来一声嘹亮的鸡鸣,我猛地醒了过来。
刚睁眼,我就对上爷爷那张青白的面容。
原本盖好的棺椁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推开一条缝,我正趴在棺材板上,和爷爷面对面。
又一阵阴风吹来,灵堂的窗户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打开了。
我浑身一激灵,突然想起爷爷交代我做的事。
我咬了咬牙,起身往灵堂外走去。
3
月亮躲在云层里,只有稀疏的月光透过云层落在地面上。
蝉鸣声不绝于耳,明明是炎热的夏季,竟然会让人觉得有些阴冷。
我抬头看了看天色,心中暗惊。
我只睡了那么一会儿,醒来时竟然已经是五更天了。
再过一会儿,公鸡就要打鸣了。
我拢紧衣裳,加快脚步往爷爷屋里走去。
门被我「吱呀」一声推开,月光顺着门缝照进爷爷空荡荡的房间里。
爷爷的东西都被收了起来,堆在房间的角落,只等着明天火化时一起烧掉。
房间里只剩下几件木制家具,还有爷爷那箱一直珍藏着的木偶。
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把箱子拿了出来,却发现上面已经落了锁。
我有些奇怪,却也顾不上那么多,脑子里只有爷爷交代我的事。
好在这把锁只是市面上最普通的铁锁,就算没有经验的人也能轻松把它撬开。
我找来一根铁丝,往锁孔里怼。
「咔嗒咔嗒」两声,锁开了。
一个木偶突然掉了出来,砸在我的脚背上。
凉气扑面而来,我被吓了一跳,手一松,箱盖重重落下。
「砰!」
这声响就像一声惊雷,在寂静的夜里尤为醒目。
我赶紧捡起那个木偶,发现这正是我昨天弄坏的那一个。
它的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人用胶水修好,纹丝不动地粘在他的脖子上,看起来十分僵硬。
就像爷爷一样。
惨白的月光下,它的表情看起来十分诡异。
平日里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木偶,此刻正扬起它那血红的嘴,直勾勾地盯着我笑。
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迅速把它塞进衣服里。
余光往箱子里一扫,我竟然在箱子里看见一个断了腿的木偶。
正想把那木偶拿出来细细观察时,肩上突然被人拍了一下。
4
一转头,就对上一张面无表情的脸。
我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吓了个半死:
「爹,你怎么在这儿?」
他坐在轮椅上,高深莫测地看着我:
「我还要问你呢,你大半夜不好好守灵,跑来这里干什么?」
不知为何,我突然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
刚想把爷爷托梦的事告诉他,脑海里就想起爷爷说的那句话:
「别让任何人知道。」
话到嘴边拐了个弯儿,我尬笑两声:
「没,我就是突然想看木偶了。」
他瞥了我手里的木偶一眼,冷哼了一声:
「你不是都见过那么多回了,有什么好看的?」
「赶紧把东西放回去,这可是祖上留下来的。」
手里的木偶被他抢过,连带着坏掉的那个都被放回了箱子里。
我身形一顿,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爹转头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又在箱子上锁上一把新的铁质锁:
「你怎么了?」
我摇摇头,眼神却盯着箱子上的锁,想着怎么才能完成爷爷的叮嘱。
爹又把箱子放了回去,不耐烦地催促:
「没事就赶紧回去接着守灵,天一亮就要启程把爷爷送去火化了。」
见再无转圜的余地,我只好乖乖应下,回了灵堂。
直到送灵时,爹才从爷爷的房间出来,
几个壮汉抬着爷爷的棺椁,我在前头领着路,爹跟在队伍后头,一路把爷爷送进了火葬场。
火舌疯狂席卷一切,我看了眼站在身边的阿爹一眼,心里突然有点不安。
为什么不让别人知道爷爷的死因?
为什么着这么着急给爷爷办后事?
为什么一个要我烧掉木偶一个却又阻止我?
他们到底还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
爹一定都知道,可他绝对不会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5
正愣神间,村东口的张婶突然找上了门。
她拉住我的袖子,一脸喜庆:
「小李啊,俺媳妇翠芽生了个大胖小子,俺想请你们去俺家唱出木偶戏庆贺庆贺。」
我皱着眉:
「我前两天刚听说翠芽生娃的时候难产,怎么现在又要办喜事了?」
「再说了,我爷爷昨天刚走,怎么给你们唱戏?」
张婶脸上的笑差点挂不住:
「可翠芽本来早几天就生了,是因为你们张家出了事儿才拖到今天的,再拖下去怕是不行啊。」
我皱眉:「怎么不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非要庆生吗?」
我眼睛一扫,瞥见她胳膊上发黑的伤口:
「你这手怎么了?」
张婶没搭理我。
她慌乱地捂住伤口,转头一脸为难地看着爹:
「李哥,你们家现在你最大,你看这事儿咋办啊?」
「再说了,我看李老爷子那样,应该也是被木偶这事儿害的吧,所以你才那么急着下葬。」
「这事儿,可得赶紧解决呀。」
我一脸疑惑,难道张婶知道些什么?
我刚想要追问,却被爹打断。
他沉思良久,最后终于下定决心:
「这样吧,张婶。你回去准备准备,我们今晚就过去。」
听了这话,张婶喜出望外,连声应好,着急忙慌地走了。
我有些不满:
「爹,你应下做什么?我们家只有爷爷一个人会这木偶戏,现在爷爷刚去世,哪有人来给她演这木偶戏呀?」
爹瞥了我一眼:
「你不是会吗?」
「我记得你爷爷小时候教过你啊。」
我愣住:
「我只学了点皮毛,怎么能上台演戏啊?而且我都已经好几年没碰那东西了。」
「再说了,我们家刚死了人,就跑去喜宴上庆祝,不合适吧?」
爹有些不耐烦:
「让你去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反正那玩意儿也不是给人看的,你随便演演就行。」
我愣住:「这话什么意思?木偶戏不给人看还能给谁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