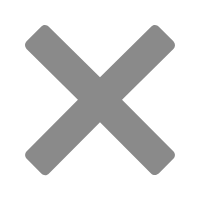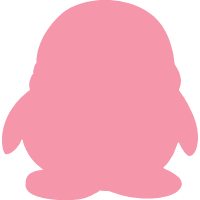-
老公要给仇人的猫办满月酒
本书由智阅文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01
隐婚第五年,秦斯远大张旗鼓的迎娶了当年抛弃自己的金丝雀。
他在我面前指天发誓,说自己只是拿她给我和女儿当挡箭牌。
以防仇家恶意中伤我们。
我点头说好。
秦斯远如释重负的把我搂进怀里:
“等我管理好手上的产业,一定立刻公开我们之间的关系,绝不叫你和女儿再受委屈。”
“至于那只金丝雀你也大可放心,当年她弃我于不顾,如今我绝不会对她心慈手软。”
放心?
倘若不是那张满月礼的请柬,我就真的信了。
婚礼外,我看着两人并肩而行,宛若一对璧人的模样时。
办好了出国的签证。
1.
带着女儿改名回来时,秦斯远正在请柬上一张张的签名。
他的书法很好,墨宝在市面上一张难求,就连女儿考第一的卷子都得不到他的签字。
现在却像不要钱似的,一张接着一张签在请柬上。
女儿捧起一张请柬,还没说什么,就被秦斯远一巴掌拍在手上。
小小的孩子一瞬间眼中蓄满了泪。
秦斯远却跟没看见似的,皱着眉训斥:
“爸爸平时怎么教你的?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洗手,不然会把细菌传给别人的。”
别人?
别人是谁?
请柬上的“程鸢”二字深深刺痛了我的双眼。
是他那只面上厌恶,私底下却给女儿起名“秦念鸢”的金丝雀?
还是那金丝雀生下的千娇万贵的孩子?
我把女儿哄回房,再出来的时候,秦斯远依旧冷着脸不断地指责:
“都是你把她惯坏了,这点教导都忍不了。以后出了社会,我看她怎么办。”
秦斯远是一个严肃的父亲,女儿打小看见他就直发怵。
我一直以为他就是这么个性格,还不断安慰自己严父慈母也算是一对教育孩子的好配置。
直到今天,我看见他写请柬时眼中浓浓的慈爱,才发现自己错得离谱。
“她今晚不许吃饭。”
秦斯远一锤定音,然后又支使我:
“你去把主卧腾出来。”
“然后再去弄一点生腌,食材我已经买好了。”
我站着没动。
他终于舍得把目光从请柬上撕下来,撩起眼皮看我一眼。
有点兴师问罪的意味:
“你之前不是答应的好好的吗?现在又要反悔了?”
“一家之主”面前,我哪里有反悔的资格。
或许是我的眼神太过冷淡。
秦斯远注意到了,轻轻的“啧”了一声:
“程鸢孤身一人很多年,哪里来的孩子?这满月礼是给她的猫办的,毕竟只有我这里足够声势浩大,才能保障你们母女俩的安全。”
说的简直比唱的都好听。
正打算回房,忽然看见了秦斯远的手机屏幕。
上面是一个面容模糊的,从监控上截下来的女人。
看到她的那一刻,我的大脑一阵轰鸣。
隐婚五年,虽然秦斯远没有给我名分,却给足了我安全感。
下班准时回家,从不参加应酬,拒绝身边所有狂蜂浪蝶。
唯有一次。
秦斯远出差,我发烧睡得迷迷糊糊,半夜下床给自己倒水喝。
却发现秦斯远在客房里,咬着牙,掐着一个女人的脖子说绝不会原谅她。
一边又流着泪和她做恨。
原打算上前仔细看看,谁料竟然晕了过去。
再醒来我躺在病房里,秦斯远坐在床边熬的双眼通红。
他说他今早一回来就看见我倒在地上。
我心中仍有疑虑,四处探问。
可秦斯远的助理和合作伙伴都能证明,那个晚上他在谈生意。
原以为是自己病糊涂了,做了个噩梦就分不清梦境与现实。
现在看来,那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他们早在那么久以前就已经勾搭在一起了。
2.
“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话?”
秦斯远重重推了我一把。
腰撞在餐桌的尖角,坐在地上一瞬间说不出话。
“沈溪,你以前可是体操队的,平衡感一流,现在在这碰什么瓷?”
我的心口一窒,腿上的伤口仍隐隐作痛。
他只记得我是体操队的,却忘记当年为了帮他挡下那根从高空落下的钢筋。
我的大腿被贯穿,这辈子再也无法重回队伍。
“秦斯远,你有没有心?”
眼泪夺眶而出的时候,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屋里跑出来。
哭的小脸通红,几乎喘不过气来:
“爸爸妈妈不要吵架,都是思思的错……”
我心疼的把女儿搂进怀里,暗暗埋怨自己怎么能在孩子面前吵架。
秦斯远却事不关己一般站在一边。
唯独在听见名字之后眉眼才有了一丝波澜。
“什么思思?你改名字了?”
我搂着女儿无意解释,秦斯远正要追问,门铃却忽然响起。
程鸢咬着唇低着头站在门口,身后是十几个全副武装的保镖。
秦斯远的眸中划过一丝暗光。
不顾我的腰伤一把将我搂到怀里,故作冷漠地看着她:
“看见我老婆不知道喊人吗?规矩都学到哪里去了?”
可在看见她通红的双眼那一刻起,冷漠就再装不下去。
“行了,哭什么?沈溪,去把生腌端出来。”
我看了看缩在墙角,红肿着眼睛的女儿,咬了咬牙去厨房里忙活。
至少不能让孩子担惊受怕。
出来时男人正想方设法哄程鸢高兴。
看见我,秦斯远扫了一眼那盘数量不多的生腌,忽然开口:
“你没有发现吗?女儿不见了,我刚刚好像看见她偷偷出门了。”
我的脑中一阵轰鸣。
鞋都顾不上穿,光着脚下楼。
别墅区大的令人绝望,又人烟稀少。
我边喊边跑,碎石刮烂了脚底的皮肉,鲜血滴滴答答撒了一地。
乌云聚拢,腿上狰狞的伤口又开始隐隐作痛。
可我一步都不敢停下。
无数社会新闻在我脑海里循环播放,挥之不去。
天渐渐黑下来了。
大雨将我浇成了落汤鸡。
一身湿淋淋地回去,程鸢不知所踪,秦斯远坐在沙发上,餐桌上一片狼藉。
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回到卧室,却忽然在衣柜里发现了熟睡的女儿。
我激动的快要跳起来。
顾及着身上的雨水,不敢轻易去抱女儿,一溜烟的跑到客厅,兴奋地和秦斯远说:
“我找到女儿了,女儿找到了,她在衣柜里睡着了!”
他冲我比了个“嘘”的手势:
“程鸢睡着了,你小声点。”
“找到就找到了,叫什么叫?我下午就看见她在衣柜里面了。”
我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你说什么?”
“我故意不告诉你的,专治你这种眼瞎的。”
怒火上涌,我紧紧咬着后槽牙,恨到全身发抖。
恨不得现在就上去扇他两耳光的时候,女儿难受的哼唧声把我拉回现实。
她躺在衣柜里,脸上大片大片的疹子,呼吸困难,意识都要烧光了。
“秦斯远!你给孩子吃什么了!”
3.
我从衣柜里扯了两件衣服隔着,小心翼翼将女儿抱起来。
额头滚烫。
秦斯远坐在沙发上,理了理微皱的衬衣,一副漠不关己的姿态:
“我怎么知道?”
“这丫头一向嘴馋,说不定趁我不注意偷吃了什么也未可知。”
后槽牙咬的咯咯作响。
我从未有一刻像现在这样恨眼前这个男人。
一手搂着孩子一手去打120,隐约带着哭腔的声音终于触动了那个冷漠的男人。
秦斯远有些犹豫的站起来,探着头往我手里看:
“不就是一颗安眠药吗?有这么严重?”
“安眠药?”
我觉得我快要窒息了。
“你给这么小的孩子喂安眠药,你疯了!你知不知道里面可能有成分会导致孩子过敏!”
五年来我从未对他大声讲话,所以现在秦斯远被我的咆哮声吼懵了。
有些磕绊地给自己找补:
“这丫头又馋又不懂事,我怕她非要上桌和程鸢抢生腌,所以才给她牛奶里放了一颗安眠药。”
“沈溪这全都怪你,谁叫你磨蹭那么大半天结果最后弄了那么小一盘出来。”
我没想到这盆污水还能泼到我的头上。
一瞬间大脑像死机了一样,半天说不出话。
捡起桌上的烟灰缸不管不顾地冲着男人扔过去。
秦斯远躲开,碎片溅到刚刚洗澡出来的程鸢脚边,吓得她惊声尖叫。
秦斯远长腿一迈,单膝跪地撩起程鸢的睡袍。
看见她腿上细如头发丝的伤口脸色一变。
黑着脸站起来,声音像数九天的雪一样寒冷:
“给她道歉。”
我顾着怀里的女儿置若罔闻。
秦斯远哄着程鸢去处理伤口,随后一把将女儿从我怀里拖出来扔到一边。
在我扑过去的时候扯住我的头发,重重两个耳光扇在脸上。
耳朵里嗡鸣阵阵,他的声音仿佛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
“我说,给,程,鸢,道,歉。”
怒从心起。
我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力气,指甲在秦斯远的手臂上留下了长长的几道血痕。
趁着他吃痛的时候,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
“去你妈的。”
程鸢和120的来电同时阻拦了我们俩继续混战。
我仍听不清声音,只好把手机免提开到最高。
医生很无奈:
“现在下着暴雨,救护车都被淹了一半,别墅区太过偏远,我们很难过去。”
女儿已经开始口吐白沫了。
我狠狠掐着手心,让自己镇定下来。
陡然想起秦斯远还有一搜直升机。
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我扑过去拽住他的衣角:
“快,你有直升机,快用直升机救救我们的女儿,送她去医院!”
“她,她才三岁啊!”
三岁,可以躺在妈妈怀里撒娇。
可以耍赖在饭前多要一袋零食。
唯独不能像现在这样,躺在沙发上,生死不知。
秦斯远一根根掰开我的手指,带着胜利者的姿态:
“除非,你先和程鸢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