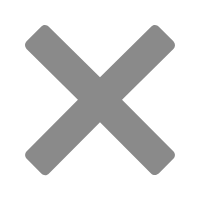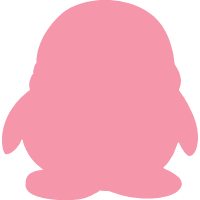-
我一尸两命后,京圈太子爷疯了
本书由智阅文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01
为了给我病危的父亲续命,我签下一纸赌孕协议。
嫁给京圈太子爷傅祈年,做他三年名义上的妻子。
条件是,为他生下一个孩子。
事成之后,我会拿到一笔足够给我父亲续命,以及让我家族企业起死回生的钱,然后,体面地消失。
所有人都说我疯了,拿自己的肚子当跳板,妄图飞上枝头。
我只是笑笑,不说话。
毕竟,在他们眼里,傅祈年是天边月,遥不可及。
而我,温冉,只是一个破落户的女儿。
他们不知道,这桩婚事,是我赢来的。
用我和他白月光吴沁妍打的一个赌,赌谁能先怀上他的孩子。
我赢了。
后来我才知道,吴沁妍只是不想生。
她怕疼,怕妊娠纹,怕身材走样。
而我,不过是他们精挑细选出来的代孕工具。
孕期第八个月,傅祈年将离婚协议推到我面前。
“孩子生下来,签了它,你可以滚了。”
我看着他,轻轻地笑了。
生产那天,医院下了病危通知。
我买通医生,给自己安排了一场盛大的“一尸两命”的压轴大戏。
1.
京圈傅家,百年望族,规矩大得能压死人。
我嫁进来的第一天,傅祈年的母亲,那位雍容华贵的老太太,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她端坐在黄花梨木的太师椅上,手里捻着一串沉香佛珠,眼皮都未曾抬一下。
“我们傅家不认什么爱情,只认血脉。你的任务只有一个,生下长孙。安分守己,别动那些不该有的心思。”
她身边的管家递给我一张黑卡。
“太太,这是先生给您的,没有额度限制。”
我垂下眼,双手接过。
“谢谢妈,谢谢先生。”
我的顺从,似乎取悦了她。
她终于舍得掀起眼皮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如同打量路边流浪狗。
“去看看你的房间吧,祈年今晚会回来。”
我住的房间在别墅三楼,大得空旷,布置得金碧辉煌,唯独没有人气。
这是我和傅祈年的婚房,可里面,没有一张我们的合照。
衣帽间里挂满了当季高定,梳妆台上摆着全套顶级护肤品,每一件都价值不菲,但都与我无关。
这些,都是“傅太太”这个身份的标配,而不是给温冉的。
我等到凌晨三点,傅祈年才回来。
他身上带着一股清冽的酒气,和一丝若有若无的女士香水味。
那款香水,我知道,是吴沁妍最爱用的夜空。
他没看我,径直走向浴室。
水声哗哗响起,隔绝了所有交流的可能。
那天晚上,他履行了作为丈夫的义务。
全程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吻。
黑暗中,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价值百万的水晶灯晃来晃去。
我告诉自己,温冉,这是交易,别谈感情。
一个月后,验孕棒上出现了两条清晰的红线。
我怀孕了。
我把验孕报告拿给傅祈年看。
他正在接电话,眉头微蹙,语气却是我从未听过的温柔。
“沁妍,别闹,我今晚就过去陪你。”
挂了电话,傅祈年才把目光投向我手中的报告单。
他只是扫了一眼,脸上没有任何为人父的喜悦。
“知道了。”
他淡淡地应了一声,拿起西装外套就准备出门。
“今晚我不回来了,你自己吃饭。”
“祈年。”我叫住他。
他回头,眉头皱着。
“还有事?”
“你……”我顿了顿,还是问出了口,“你爱过我吗?哪怕只有一点点。”
他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温冉,摆正你自己的位置。”
他的声音,像是冬日里的寒冰,轻易就将我心里那点可笑的奢望,冻得梆硬。
“你不过是我花钱买来的一个子宫。别对我有任何不该有的幻想。”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
手里的报告单,被我捏得变了形。
原来,我的成功,在他眼里,不过是完成了一项传宗接代的任务而已。
2.
我开始安安心心地养胎,扮演好一个合格的傅太太。
我对傅老太太言听计从,对家里的佣人温和有礼。
我甚至会主动给傅祈年发信息,提醒他天气变化,让他注意身体。
我的懂事,让所有人都很满意。
傅老太太看我的眼神,终于有了一丝温度。
傅祈年回家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他对我依旧冷淡,但至少,他愿意和我同桌吃饭,愿意在长辈面前,与我扮演一对恩爱夫妻。
一次家庭聚会,他的堂妹指着我身上的裙子,笑得一脸天真。
“堂嫂,你这条裙子是去年的旧款了吧?我前几天看到沁妍姐穿了最新款的,真好看。”
饭桌上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
我正想开口解围,傅祈年却先我一步开了口。
他的声音很冷。
“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堂妹被他训得缩了缩脖子,不敢再说话。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维护我。
哪怕,只是为了他自己的脸面。
可我心里,还是有了一丝异样的感觉。
或许,他也不是那么讨厌我。
直到那天,我无意中在他的书房里,发现了一份文件。
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
他将自己名下百分之十的股份,无偿转让给了吴沁妍。
而协议的签订日期,就在他为了我训斥堂妹的第二天。
原来,他不是在维护我。
他只是觉得,他的白月光吴沁妍,不该被人拿来和另一个女人比较。
我的那点动容,成了一个笑话。
我将文件放回原处,不动声色地退出了书房。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抱着刚出生的孩子,站在悬崖边。
傅祈年和吴沁妍站在我对面。
傅祈年对我说:“把孩子给我,然后你从这里跳下去。”
我笑了,抱着孩子,纵身一跃。
醒来时,我浑身都是冷汗。
我摸着自己已经高高隆起的腹部,感受着里面小生命的胎动。
我的孩子。
我绝对不会,把他交给任何人。我开始频繁地去医院做产检。
每一次,我都要求同一个医生。
那个医生,姓李,是我父亲的过命之交。
当年我家出事,所有人都避之不及,只有李叔,还愿意念着旧情,帮了我们一把。
我找到他,将我的计划,和盘托出。
李叔听完,沉默了很久。
他看着我,叹了口气。
“冉冉,你这又是何苦?”
“李叔,”我打断他,“我没有退路了。”
李叔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我尽力。”
有了他的保证,我心里的最后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孕八月的时候,傅祈年带我去了商场。
他说,要给孩子买点东西。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出要为孩子做点什么。
我看着他在婴儿用品区里,认真地挑选着婴儿床和衣服。
他的侧脸,在商场明亮的灯光下,显得格外英俊。
有那么一瞬,我几乎要以为,我们会是寻常的一家三口。
可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
他之所以这么做,不过是为了安抚即将临盆的我。
为了让他心爱的吴沁妍,能顺利地得到一个健康的孩子。
“喜欢这个吗?”他拿起一个小小的拨浪鼓,在我面前晃了晃。
我看着他手里的拨浪鼓,没有说话。
他似乎有些不悦。
“怎么,不满意?”
我摇了摇头,轻声说:“太吵了。”
他顿了一下,将拨浪鼓放了回去。
“那就买个安静点的。”
他转身去挑别的玩具,没有看到我眼底一闪而过的嘲讽。
傅祈年,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的孩子,喜欢什么,害怕什么。
因为,你根本不配做他的父亲。
3.
傅家老宅的晚宴,水晶灯的光辉流淌在每一个角落,却照不进人心。
我端着一杯温水,安静地坐在角落的沙发里,腹中的孩子今天格外闹腾,一阵阵的胎动让我背脊见了汗。
“温冉。”
傅祈年叫我的名字,声线平直,听不出什么情绪。
我抬起头,他站在不远处,身形挺拔,西装剪裁得体,正与几个生意上的伙伴谈笑。
他身边站着吴沁妍,一袭白色长裙,温婉动人。
她才是这场宴会的主角,即使她输了那一纸孕赌。
我扶着腰,慢慢站起来。
傅祈年对我招了招手,示意我过去。
他的朋友们目光各异地落在我高高隆起的腹部,又很快移开,带着几分探究,几分了然。
“给大家介绍一下,”傅祈年的手搭在我的腰上,力道很轻,“我太太,温冉。”
我扯出一个得体的笑,对众人点头。
“傅太太好福气,”一个微胖的男人笑着说,“这肚子看着,就快生了吧?”
“下个月。”我轻声回答。
“那可要恭喜傅总,双喜临门了。”
傅祈年脸上没什么喜色,只淡淡应了一声。
他的手从我腰上滑落,转而很自然地替吴沁妍理了理鬓边的碎发,动作亲昵。
“沁妍,刚才说你看中了那套星夜,回头我让人给你送过去。”
吴沁妍羞涩地笑了,声音又软又甜,“祈年,那太贵重了。”
“你喜欢就好。”
他的声音里,是我从未听过的温柔。
那套名叫星夜的珠宝,我前几天刚在杂志上看到,全球限量三套,价值连城。
宾客们的眼神在我跟吴沁妍之间来回打转,同情,讥诮,看热闹,什么都有。
我的脸皮一阵阵发烫,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我像封建社会里不受宠的主母。
我扶着腰,想找个借口先行离开。
“温冉,”傅祈年却叫住了我,他从侍者的托盘里拿起一杯香槟,递到我面前,“去给陈董敬杯酒,城南的项目,陈董出了不少力。”
我看着那杯酒,里面的气泡正争先恐后地向上涌。
抬头满是惊愕,“我怀孕了,不能喝酒。”
傅祈年的眉心微微蹙起,透出几分不耐。
吴沁妍拉了拉傅祈年的衣袖,适时地开口:“祈年,姐姐为傅家怀了长孙,那可是天大的功劳,现在身子不方便,就别为难她了。我去替姐姐敬陈董吧。”
她说完,还对我露出一个歉意的微笑,仿佛在说“你看,我又帮你解围了”。
傅祈年看了看我,越来越厌恶。
“你除了会怀孕还会干什么?”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拗不过傅祈年的无理,我端起一杯清水,走向陈董。
一个五十来岁,脑满肠肥的男人,一双小眼睛在我高高隆起的肚子和傅祈年的脸上来回打转,透着精明和谄媚。
“陈董,我敬您。只是我身子不便,这杯以水代酒,您多担待。”我举起杯子,笑容得体。
陈董哈哈一笑,油光满面,“傅太太这话说的,太见外。傅总今晚高兴,你怎么也得眯一口,沾沾喜气嘛!”
他嘴上说着,眼睛却瞟向傅祈年,寻求主子的示下。
傅祈年正低头给吴沁妍拢了拢披肩,闻言连眼皮都没抬一下,“陈董是长辈,让你喝是给你面子。”
“面子就一个,给了我陈董不要了?”
4.
空气有片刻的凝滞。
陈董的笑僵在脸上,胖脸涨成了猪肝色。
他一个混迹商场的老油条,竟被我这个看似温顺的傅太太当众下了面子。
“你这个女人,怎么说话的!”他恼羞成怒,胖大的身子朝我逼近一步,伸手就要来抓我的胳膊,“给你脸你不要脸!”
我早有防备,扶着腰往后一撤。
他扑了个空,脚下一个踉跄,肥硕的手掌重重推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闷哼一声,整个人向后倒去。
视线天旋地转间,我只来得及护住自己的肚子。
手中的玻璃杯脱手飞出,划出一道清亮的弧线。
“啪”的一声脆响,杯子摔在地上,四分五裂。
杯里的清水,不偏不倚尽数泼在了吴沁妍那条价值不菲的白色长裙上。
“啊……”吴沁妍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胸前湿了一大片,布料紧紧贴着皮肤,狼狈不堪。
全场哗然。
傅祈年脸色一变,想也没想就冲到吴沁妍身边,紧张地上下打量,“怎么样?有没有事?”
吴沁妍白着脸,摇了摇头,却第一时间指向躺在地上的我,满眼焦急,“我没事,祈年,你快看姐姐!她还怀着孩子呢!”
多好的演技。
傅祈年这才把目光转向我,那眼神充满责备。
我躺在冰凉的地砖上,腹部传来一阵阵熟悉的坠痛,但我没动,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看着他如何处理这出闹剧。
“道歉。”他对着我,吐出两个字,声音里没有一丝温度。
“我大着肚子摔倒在地,你不第一时间照顾我,反倒去看她有没有事,那是一杯水,不是一杯硫酸!”
“少拿你的肚子说事,摔了一跤你不是也没见红,现在还中气十足地和我犟嘴。”
“道歉!我不想再说第三遍。”
我撑着胳膊,慢慢从地上坐起来,仰头看着他,和被他护在身后的吴沁妍。
然后,我对着吴沁妍,露出了一个歉意十足的微笑。
“对不住了,吴小姐。”
回到房间,我脱下高跟鞋,双脚早已被磨得通红。
空旷的卧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呼吸的声音。
腹中的孩子又动了一下,这一次,力道很重,顶得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冲进卫生间,抱着马桶吐得天昏地暗。
孕早期的反应早已过去,可最近不知为何,孕吐又卷土重来,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猛烈。
胆汁都快要吐出来了,喉咙里火辣辣地疼。
我瘫坐在冰冷的地砖上,浑身脱力,眼前阵阵发黑。
手机响了,是傅祈年打来的。
我扶着墙,挣扎着站起来,按下了接听键。
“上来,给我煮碗醒酒汤。”他的声音带着命令的口吻,没有一丝关切。
“张嫂不在?”我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我只想喝你煮的。”
他说完,便挂了电话。
我对着镜子,看到一张苍白憔悴的脸。
曾几何时,就是这么一句话,能让我高兴得半宿睡不着。
我以为,那是我在他心里,独一份的特别。
那是在我们刚结婚不久,他还愿意对我展露片刻温情的时候。
有一次他应酬喝多了,我笨手笨脚地给他煮醒酒汤,切姜片时还划破了手。
他靠在厨房门口,看着我包扎伤口,眼里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他说:“以后,我的醒酒汤都由你来煮。”
我把那句话当成了一辈子的承诺。
如今再听,只觉得胃里那股恶心劲儿又翻了上来。
我扶着墙,一步步挪下楼。
偌大的厨房灯火通明,张嫂正在擦拭灶台,听到我下楼的动静,她惊得回过头。
“太太,您怎么下来了?想吃什么,我给您做。”
她快步走过来扶住我,语气里满是藏不住的担忧。
“您的脸色……怎么白成这样?”
我摆摆手,声音气若游丝。
“没事,我给先生煮碗醒酒汤。”
张嫂的脸色变得很古怪,欲言又止地看着我,眼里全是同情。
“太太,这……”
“怎么了?”
她低下头,不敢再看我的眼睛,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先生……刚刚跟吴小姐出去了。”
我的手,就那么僵在了半空中。
张嫂绞着手指,声音更低了。
“吴小姐说她的猫好像不舒服,先生一听,就马上开车陪她去宠物医院了。”
“走的时候还交代,说今晚不回来了。”
窗外起了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
我站在空无一人的厨房里,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5.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卧室的。
躺在冰冷的床上,腹中的孩子像是感受到了我的情绪,也安静了下来。
后半夜,我被一阵剧烈的腹痛惊醒。
冷汗瞬间浸湿了睡衣。
我挣扎着去拿床头的手机,想给傅祈年打电话。
可拨号页面停留在他的名字上,我却迟迟按不下去。
他在陪吴沁妍,我这时候打电话过去,只会让他更厌烦我。
痛楚一阵比一阵密集,我咬着牙,自己拨通了李叔的电话。
李叔很快赶到,检查过后,神色凝重。
“冉冉,你有早产的迹象,必须马上住院观察。”
我被送进医院,躺在惨白的病床上,看着一袋又一袋的安胎药输进我的身体。
李叔告诉我,我的情绪波动太大,影响到了孩子。
他问我:“傅祈年呢?这种时候,他应该陪在你身边的。”
我能怎么回答?
我的先生,正陪着另一个女人,为她生病的猫彻夜不眠。
而我,和他血脉相连的孩子,在他心里,或许还不如一只猫重要。
我在医院住了三天。
这三天里,傅祈年一个电话,一条信息都没有。
第四天,傅家的司机来接我出院。
车子驶入傅家老宅时,我看到傅祈年的车停在院子里。
他回来了。
我走进客厅,他正坐在沙发上,吴沁妍也在。
她依偎在他身边,手里捧着一个青花瓷的瓶子,正小心翼翼地往里面插花。
那瓶子我很眼熟,是傅祈年从拍卖会上高价拍回来的古董,他平日里宝贝得紧,连我碰一下都不许。
现在,他却任由吴沁妍拿来当花瓶。
看到我,傅祈年只是抬了抬眼皮,语气平淡地问:“出院了?”
“嗯。”
“身体没事了?”
“没事。”
简单的两句对话,再无其他。
他甚至没问我为什么会住院。
吴沁妍站起身,走到我面前,脸上带着关切,“姐姐,你脸色好差,怎么了?”
我看着她,没说话。
“前几天听说姐姐住院了,我和祈年本来想去医院看你的,可是……”她咬了咬唇,一脸为难,“我的猫病得很重,离不开人,祈年只好一直陪着我。”
她顿了顿,又补充道:“姐姐你不会怪我吧?”
我轻笑了一声,吴沁妍脸上的笑意僵住了。
“怎么会呢?”
“你的猫,当然比我和我肚子里的加起来都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