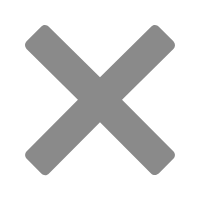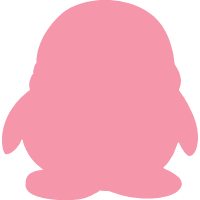-
花魁移情别恋后,我亲手撕碎她的卖身契
本书由智阅文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01
为了林月漪的一句“先立业再成婚”,我花了整整五年时间将她捧成京城第一花魁。
可在太后下旨赐婚时,她看都没看我一眼,直接在婚书上写下了穷书生柳越霖的名字。
林月漪说,柳越霖能欣赏她的才情,而我只会衡量她的价值。
可她忘了,如果没有我,她不过是乐坊角落里一名无人问津的舞姬。
她登上云端的台阶,每一寸都是我铺就的。
既然她不想要这登云梯,那我便重新把她拖回烂泥里!
1.
太后的赐婚懿旨刚下不久,乐坊门前就挤满了来看热闹的百姓。
这场婚事本该是我和林月漪多赢的一桩美谈。
只要她在婚旨上写下‘裴墨卿’三个字,我们多年的情谊便能修成正果;
借着太后赐婚的殊荣,‘月漪娘子’的名号必将响彻熙都,乐坊的生意也能更上一层楼。
可她偏偏写下了那个穷书生——柳越霖的名字。
一夜之间,我成了全京城的笑柄,乐坊账面上更是直接损失了三万两白银。
那些冲着‘京城第一花魁’名号投资的商贾们拼着缴纳高额违约金的代价也要纷纷撤资毁约。
这也难怪,毕竟京城无人不知——
月漪娘子的一支《霓裳》能带火苏杭十家绸缎庄;
她随口吟的半阙《金缕》,能让西域香料价格翻上三倍;
就连她不经意的一句‘夜来香气薄’,都能让东街脂粉铺的茉莉膏滞销三千盒。
商人重利,眼见林月漪成婚后要离开乐坊,没人想做赔本的生意。
我面无表情地翻看着一张张毁约的契书,忽然指间一顿——在一堆文书中,竟发现了一张字迹清丽的七言,看着像林月漪亲笔。
“金笼铸就困花枝,五载春风误岁时。
明珠蒙尘权作砾,清商谱尽商人词。”
好一句‘困花枝’,好一句‘商人词’!
她仅用几句诗就将我这五年的心血轻描淡写地贬作了一场买卖。
我嘴角笑意渐冷,捏着花笺的指节发白:
“传话出去!”
“即日起,乐坊十二楼与林月漪——恩断义绝!”
小厮面露慌张:
“公子三思!月漪娘子的身契还有三个月才到期,眼下正是熙都乐坊评比的关键时候,若这时放出消息,恐怕乐坊的损失……不可估量!”
“我现在还怕损失?”
我冷笑一声,将契书重重扔在桌上:
“京城从不缺才貌双全的女子,既然她不识抬举——那京城第一花魁的位置,换人!”
小厮俯身退去,我望向窗外出神,五年前初遇林月漪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那时的她还是乐坊最末等的舞姬,连登台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在角落里独自练习。
我偶然路过乐坊,对这个跳错步子就眼泪汪汪的小姑娘一见钟情。
我提出为她赎身迎她入门时,她并未拒绝。
只说时机不到,待她成为名动京城的第一花魁后,再同我成婚。
这话让我掏空家底建起乐坊十二楼,买断她的身契,再延请名师教习。
她确实天赋过人,第一次登台就惊艳四座。
那晚我们躲在后台,她沾着胭脂在我掌心写下婚约。
可京城的水远比我想象中还要浑。
尚书公子要强纳她为妾,我阻止,被打断两根肋骨;
淮阳王在茶里下药,想逼良为娼,我当众掀了整桌茶点。
可即便这样,在她如愿成为花魁后,还是将婚期一推再推。
直到那日,我撞见她把仅有一面之缘的柳越霖叫进闺房中商讨曲谱。
我和她争吵,她却说:
“柳公子是读书人,只有他才知晓我的才情抱负,像你这种满身铜臭的商人只会衡量我登台的价值!”
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她不再是站在乐坊角落里练舞的小姑娘了。
可后来她又哭着跟我解释,是怕门第之差,怕我父亲瞧不上她的贱籍。
她求我谋太后赐婚,但却在如愿得偿后提出与我断绝关系。
好!既然她这么想离开,那我便看看——
没了我,她这第一花魁能在京城绽放几时?
2.
小厮离开后没多久,门口出现一道头戴幕笠的纤细身影。
“裴墨卿。”
林月漪走进来,身后跟着那个连举子都没考上的穷书生柳越霖。
“我是来赎身的。”
“赎身?”
我缓缓抬头,嘴角泛起一抹冷笑反问:
“不知月漪娘子带了多少金银,你如今名声大噪,赎身钱……可不低!”
林月漪有些愠怒:
“裴墨卿你什么意思?五年前你买断我身契的时候明明答应过,等我赎身那日,你不会在银钱上为难我,你现在是想反悔不成?”
“当时的前提是你我有婚约在身,如今你改嫁他人,我为何要做这赔本买卖?”
我意味深长地看了眼她身后的柳越霖,林月漪立刻警惕起来:
“你想做什么?”
我笑了笑:
“别误会。我是想提醒你,根据身契规定,你作为十二楼唯一的花魁,有承担乐坊盈亏的责任。由于你的任性妄为,乐坊在一夜之间损失了三万两白银,这些都会记在你的赎身钱里。”
“你这是蓄意报复!”
林月漪将幕笠摔在地上,朝我怒吼:
“裴墨卿!你从来都没想过要娶我,你只是想把我绑在身边做给乐坊揽财的工具!”
柳越霖见状,也忍不住开口:
“裴东家,强留女子,非君子所为啊!”
我嗤笑一声:
“柳公子倒是君子,带着别人的未婚妻私奔,如今连赎身的银子都掏不出?”
“你!”
柳越霖脸色涨红被林月漪出声打断:
“够了!你眼里除了银子以外还有什么?这些年我替乐坊赚的钱还不够吗?”
“当然——不够!”
我让人叫来账房先生,一笔一笔和她从头算起:
“去年三月,你称病推掉丞相府一早定好的堂会,乐坊赔了违约金一千两。”
“今年五月,你跳舞时为了助兴摔碎了西域特产的琉璃盏,作价八百两。”
“最要紧的事上个月,因你谎报布价,导致十二家绸缎庄合计亏损两万三千两白银,这些可是乐坊出面帮你垫付的!”
账房先生的算盘敲得噼里作响,林月漪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见柳越霖又要开口,我指了指他身上做工精巧的长袍,示意道:
“差点忘了,柳公子身上这金线绣梅长袍也是用乐坊分红买的,记得一起算上!”
“裴墨卿!你别欺人太甚!”
林月漪抓着我的手腕,眼睛通红:
“这些分红都是我应得的!”
“应得?”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卖身契上特别注明,花魁所有收入五五分成。可你私藏了多少打赏?可还记得?”
我拿起账本,清了清嗓子:
“中秋宴上,你收了镇南侯府的一对翡翠镯子;乞巧节那晚的宫宴,你逗六公主开心,敏妃娘娘赏了你一枚和田玉佩和五千两白银;上元节那日,平阳郡主赏了你两盒南海珍珠……”
我每算一样,林月漪的脸色就白一分。
不知过了多久,我把账单举到她眼前:
“一共是——五万八千两白银!劳烦问一句,怎么支付?”
3.
林月漪突然笑了,她当着我的面挽起衣袖,原本印着守宫砂的小臂此时光洁无暇:
“事到如今,我不妨告诉你!我早就把自己的初夜给了裴郎,卖艺不卖身的花魁没了清白,你猜那些客人还愿意为我花多少银子?”
这话像是一道惊雷,劈得我手里的毛笔“咔嚓”断成两截。
我一把掐住她的下巴,气得声音都在发抖:
“林月漪,你真是……不知廉耻!”
她吐气如兰,眼里带着志得意满的笑意:
“怎么,裴东家现在嫌我脏了?”
我不明白当初那个咬着牙,连舞步跳错都会眼泪汪汪的小姑娘怎么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见我不说话,林月漪以为我拿她毫无办法,笑得更加张扬:
“就算你把我强留下来,也只会让你赔的更惨!裴东家,商人重利,这买卖盈亏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
我勾了勾嘴角,拇指抚过她唇边鲜红的胭脂:
“好!既然你自甘堕落——那在身契期满前,你就和下等舞姬一样,去南苑接客吧!”
林月漪的瞳孔骤然紧缩。
她猛地推开我,话都有些说不利索:
“你……你敢?”
我气的头脑发昏:
“你身契在我手中,我有何不敢?”
柳越霖也被我的话吓到:
“我与月娘成婚是太后娘娘亲自下的懿旨,你逼良为娼,就不怕太后降罪吗?”
我耸了耸肩,坐回椅子上:
“太后下的旨意是赐婚,可却从没说过要为林月漪赎身!如今她的身份仍是我十二楼里的舞姬,你们若想强行毁约,我也不怕对簿公堂!”
柳越霖脸色发白,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
我也不想与他们过多纠缠,只朝屋外喊了一句“来人!”
没一会儿,数十名家丁拿着棍子进门将林月漪和柳越霖团团围住。
“送月漪娘子回房!”
我轻声开口,家丁得令,刚准备上前,只见林月漪捂着小腹,眼中闪过一丝恐惧。
“你不能动我……我,我怀孕了!”
她声音轻得像片羽毛,落在地上却让整间屋子的空气瞬间凝固。
“大夫说我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裴墨卿,你现在让我出去接客就是杀人!”
我盯着她的肚子,怒极反笑。
两个月……正是她求我让她进宫献舞的时候!
原来我在酒桌上觥筹交错喝到意识不清,对着宫中内侍点头哈腰给她求进宫机会的时候,她就已经和柳越霖勾搭在了一起!
“好啊,真是好啊!没想到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偷情,竟然连孩子都有了!”
我抓起桌上的账本,朝二人扔了过去:
“滚!带着你的孽种,滚出乐坊!”
“七日之内若凑不齐赎身钱,我们公堂上见!”
4.
林月漪没能成功赎身的事,很快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次出门都能听见街边茶肆里飘来的闲言碎语。
有人说我是爱而不得,嫉妒林月漪和柳越霖成婚,故意刁难;
也有人说我利欲熏心,为了留住林月漪这颗摇钱树宁可鱼死网破。
更有甚者传言,说我为了报复林月漪,哄抬身价,若她不从,就把她卖进窑子里。
就连那说书先生的惊堂木下拍的也是我忘恩负义,欺男霸女的故事。
一时间我成了比土匪头子还恶的存在。
最可笑的是,林月漪为了让我声名狼藉,竟自己租了个戏台,免费为百姓弹琵琶唱曲。
她的琵琶也是我请人细心教导过的,那首柳越霖亲手为她填词的《折梅令》被她弹得婉转悠扬,在短短三日内风靡全城。
连街边卖糖人的小贩都能哼上两句:
“锦窟锁春五年整,算明珠、价秤银星。
按得商宫羽,原来铜板声!
恁道是、画堂恩重,却怎生、折了梅性?
待借东风力,掷还金缕筝!”
彼时,我站在二楼的茶馆,望着对面沉心唱曲的林月漪。
林月漪穿着素白襦裙坐抱琵琶,不施粉黛,只留一朵白梅簪在鬓角,像朵被风雨摧残的花朵,任谁看都我见犹怜。
“裴东家好狠的心肠!”
她唱到动情处,泪珠簌簌落下:“五年来我为乐坊赚下金银无数,可如今连赎身的自由都没有……”
台下顿时掀起骂声一片:
“裴墨卿真是个黑心肝的!月漪娘子每日练舞到五更,十个脚趾都磨破了也不让停歇!如今还霸着身契不放人,就该让他下大狱!”
“就是!月漪娘子别怕,我们联名上书府尹大人!定要为你讨回公道!”
听着百姓们义愤填膺的声音,小厮担心道:
“公子,醉仙楼的东家前日公然在集市上放话,但凡从十二楼转投他处的舞姬,违约金全包!短短三日,已经有三名当红舞姬被挖走,五场堂会遭退订。”
我摩挲着茶杯,笑出声来:
“还真是墙倒众人推啊!”
小厮继续道:
“今日,霓裳馆为林月漪送来了赎身钱。听说他们的东家已经私下与林月漪商量好,两个月后的乐坊花魁评比,由林月漪代替替霓裳馆比舞!”
“公子,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
我掸了掸衣袖,披上大氅,冲小厮吩咐:
“备车,去西域商会!”
5.
乐坊评比大选前,熙都城内所有参赛的乐坊花魁都来了京城。
我站在朱雀大街上看着一辆辆运载花魁的马车经过,耳边突然响起一道刺耳的女声:
“哟,这不是裴大东家吗?都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还敢抛头露面?”
林月漪挺着微凸的肚子,却仍穿着束腰舞裙,鬓角的白梅被汗水打湿,一看就是刚唱曲回来的样子。
见我转身,她音调更高:
“听说十二楼最近连个客人的影子都见不着?要不要我赏你几个铜板救济救济?”
我冷笑一声,目光扫过她浮肿的脚踝:
“林姑娘大着肚子还四处拼命唱曲,看来和柳公子婚后的日子过得很是艰辛啊!”
她脸色瞬间铁青:“至少柳郎真心待我,不像某些人,把我当赚钱的牲口使唤!”
“真心?”
我嗤笑出声,“那他个大男人不想着怎么补贴家用,反倒让你大着肚子抛头露面?”
柳越霖按捺不住,冲上前来:
“裴墨卿!你莫要血口喷人!”
“就是!柳郎是读书人,他的手是用来写字的,不是像你一样,满手铜臭,令人恶心!”
林月漪瞪着一双杏眼目眦欲裂,她歇斯底里地尖叫:
“从始至终,我不过是你养的一只鸟!你从来都只把我当个玩物!只有柳郎才是真心懂我的人!”
“嘘——别喊的这么大声!你是想让是所有人都知道昔日的京城第一花魁如今成了大肚子与人吵架的市井泼妇吗?”
林月漪面色一滞,低声威胁道:
“你要是敢让别人知道我有孕一事,我与你不死不休!”
她气得浑身发抖,扬起手就要扇我耳光却被我反手攥住手腕:
“省省力气吧!这些日子,你只顾着四处唱曲,怕是连最基础的舞步都忘了个干净!有与我叫喊的功夫不如找个没人的地方练功,毕竟你现在的身子……可不如从前轻盈了!”
林月漪脸色骤变:
“不劳你费心!”
“我曾跟随名师学舞,就算我大着肚子上台,也比你十二楼里那群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强百倍!你就等着评选结束后,成为京城永远的笑柄吧!”
我轻笑一声,转身上了马车。
马车驶向城西。
在那里,我秘密培养的西域胡姬阿依慕正在最后排练。
她足尖点地时,金铃叮当作响,比当年林月漪的成名作还要惊艳三分。
舞师躬身行礼:
“阿依慕的飞天舞,一定会成为京城新的传奇!”
我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我也很期待,三日后,谁才是京城永远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