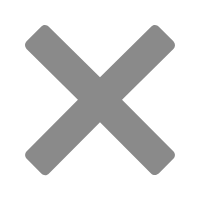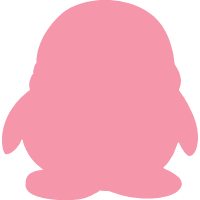-
夫君以为我只是装穷
本书由智阅文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01
我与江云淮是一对贫贱夫妻。
可江云淮实是京中素有诨名的小侯爷。
他早已看穿我正是那位喜好游戏人间的昭阳郡主,扬言要将我狠狠打脸。
小侯爷耍尽手段,没苦硬吃,逼我现出真身。
可他猜错了。
我真就又老又穷,还命不久矣。
1
屋内的暖意丝丝钻出窗柩,我推门的动作一怔。
薄薄的纸窗上,一道窈窕人影掩唇轻笑。
美娇娘声如银铃:「小侯爷真有趣。」
「你这出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戏码何时才唱尽呀?」
残旧的窗纸缝隙现出江云淮的身姿,此刻的他红裳锦袍,张扬跋扈,嗤笑出声:「早就唱腻了。」
「可只怕我那尊贵的郡主娘娘糟糠妻还不肯下台罢。」
卖身试药的第七年,县太爷的府医说我命不久矣。
何必为了痨病夫君,连自己也赔去了。
我笑得很甜,只说自己终于攒够最后一副药的药银。
因着迫切希望夫君能早一刻化解疾症,我咬牙将腕子上的银镯典当,阔气地赏银搭乘牛车上山回家。
以往试药,我皆是连夜爬山,清晨归来。
夫君重病在身,却每每披衣点烛,不辞辛劳,为我更衣,奉上热饭。
他从不嫌弃我是无人管教的孤女,大字不识的村妇。
我自当不离不弃,惟愿相携而终。
江云淮少时家贫,落下旧疾,轻易不能根治。
若是少服药汤一日、哪怕一个时辰,他也要咳血不止,卧病不起。
我不忍夫君病骨支离,饱受咳血之症折磨,白日以身试药,夜里挑灯绣花,为他攒下药银。
当初郎中诊断,若能坚持服药,七年后定有好转。
湿冷的雨水霎时浸得我浑身一颤。
今夜雨寒,简陋的茅屋内却烧着寻常人家见也见不得的银丝炭。
我的夫君江云淮身弱体轻,既受不了风,也下不了地。
因此,他与我言语时总是细语轻声,如春风拂面,似文质书生,叫人含羞。
可屋内的贵公子一脸的兴致缺缺,嘲弄的神情似是在强压着眉间的戾气:
「我与她虚与委蛇多年,此刻暴露身份,只会让她倒打一耙,反成我的不是。」
他身侧同样衣着华贵的女郎妆点如谪仙。
女子笑盈盈地让江云淮歇歇气:
「昭阳郡主性情古怪,可小侯爷也没赔上什么呀。」
「左右你这病也不是真的,隔三差五还能借口科考,回京享福。」
「可她倒是坐得住,从未回过京城,宁愿在穷乡僻壤和侯爷你做什劳子庶民夫妻,年纪大了还不回去成婚,岂不是成了老姑婆了。」
江云淮并未制止她对我的调侃,反是深以为然:
「她每隔三日便下山试药,谁不知是去花天酒地,直至半夜才悻悻而归。」
「呵,身为郡主舍不下纸醉金迷,却装作穷困潦倒,玩弄人心。」
「我这位病弱夫君苦苦守在家中,为她洗手作羹汤,她却毫无怜悯,不肯施舍半分。」
「我倒要看看我要做到何等地步,她才会满怀愧疚,向我坦诚布公。」
江云淮的不屑与轻蔑却似冷冽的风雪翩连吹刮,将我的肺腑心魂寸寸凝结。
2
夜深秋寒,我浸泡在雨中,四肢冻透僵硬。
暖意融融的屋内,江云淮却与气质高华的女娘举止亲密,莺声燕语不断。
原来,那位女娘竟是南姚太守之女,许青荷。
她与江云淮自小便有婚约。
是我这位「昭阳郡主」仗势欺人、故弄玄虚在先,强抢了她的夫君。
二人百般耍滑,只求我高抬贵手,放过这对眷侣。
可他们自顾自入戏,却不知我并非那位从不以真面目示人的郡主娘娘。
我既不曾花天酒地,也并未对夫君见死不救。
我只觉庆幸。
因为我真乃穷困潦倒的乡野村妇。
幸好夫君的病是假的,我辛苦购置的药材便可退回药局。
而那枚典当的银镯也能趁早赎回。
毕竟,那是娘亲留给我的最后一件遗物。
这些年为着江云淮看病吃药,娘亲留下的其他嫁妆早已典当干净。
我在村口截下赶牛车的汉子。
车夫是个实诚人,她愿捎我一程,只问我:「夫人,怎又赶回山下?」
我抹开脸,掌心混着雨泪与泥点:「相公有病,要请个大夫给他治治。」
「哟,那我得赶快点。」
车夫扬臂挥鞭。
我摇摇头,又揉去一把泪,好似满不在乎:「无妨,他死不了,是脑子有病。」
大雨滂沱,牛车多是载物,并无遮挡。
夜半行车,豆大的雨点鞭挞湿漉漉的蓑衣,渗透的冷雨将贴身的衣衫一遍遍洇湿。
当我敲开当铺紧闭的大门时,镇里唯有青楼酒肆歌舞不休,灯火通明。
四下寂寥,打烊的伙计不耐烦地推开门。
尽管我早已麻木到不会再次感到苦痛,扯出的笑容却不尽人意。
我迫切地问道:「公子,麻烦您看看当票上的银镯还在不在,我来赎回。」
当铺伙计却一眼认出我正是今日不顾风雨,前来典当的主顾。
他瞧我狼狈的模样,嗤笑一声:「就你那绣花针一样粗的银镯,摆上台面都嫌丢人。」
伙计话糙理不糙,我的银镯定然还留在铺头。
我双眼一亮,可伙计又言:「说来也怪,你刚典了那镯子,后脚县太爷的府医沈大人就来问你典了什么,他都买了。」
县太爷府的年轻府医沈钰,为人仁心,时常私下替我调理身体。
也是他告知我为县太爷试药积毒太深,五脏俱损,若再不用心调养,恐怕活不过这个冬天。
可笑,我却是用自己的命去换回另一个人的戏弄与侮辱。
4
江云淮自叙出身没落的书香门第,如此青年才俊却迎娶一介孤女。
我曾经很是动容,因而愈发觉得自己出身低微,高攀贵婿。
夫君品格贵重、腹有诗书,若有岳家提携,只怕迟早一飞冲天。
可真相大白,原来他从不需要一飞冲天的机遇。
江云淮本就是天之骄子。
然而他向我提亲时甚至拿不出丁点像样的聘礼。
他说,他原想上山采药为我换一副出嫁头面。
只是一介文质书生不识路况,险些跌下山崖,胳膊足踝都划开寸长的血口。
他疼得脸色青白、浑身颤抖,却心疼买药疗伤的钱,不肯医治。
我深感江云淮情深不易,亲手卖掉熬花了眼才绣好的婚服,为他请来郎中。
新婚之夜,江云淮伤口恶化,高热不退。
我彻夜不眠,候在榻前为他换药擦身,祈求菩萨保佑。
可笑的是我的夫君并非因我而伤。
他是京中来的小侯爷,初闻山有猛虎。
江云淮自诩武功高强,只身一人进山,为未婚妻取得虎皮作一身大氅。
最终他落得一身伤,却要我费尽心思与血汗才将他从阎王殿前拉回来。
可那虎皮小袄昨夜还套在许青荷的身上。
婚后逢冬,他借口身负旧疾,蜷在屋内懒得动弹。
我白日凿冰,夜里绣花,维持生计。
十指的冻疮由红转青,由青入紫,最后成为一团团冷硬的风包,再长出新的冻疮。
我自觉丑陋,不敢随意在江云淮面前伸出一双手。
可他还是看见了。
江云淮眼中的心疼不似做假。
但他的眸光很快又沉寂黯淡下去,最终换来轻飘飘地安慰:「娘子的手最好看。」
5
翌日响午,我推开家门,直直撞进江云淮清亮如水的墨眸。
江云淮唤我娘子,他的眼底是淡淡喜意。
难为锦衣玉食的江云淮屡屡为我换回粗布麻衫。
可饶是如此,我的夫君身姿出挑,行止优雅,足见京中世家子弟的绰约风姿。
江云淮分明离开了京城,可京城的繁华绮丽并未离开他分毫。
偏我见识浅短,从未识破他的伪装。
他嘴上一如既往心疼我赶集奔波,为我端出热腾腾的清粥小菜。
江云淮的一切都是假的,唯有他为我下厨不曾作伪。
成婚以来,我的饭食皆由江云淮亲力亲为。
可金尊玉贵的小侯爷的厨艺糟透了。
粟米蔬肉、油盐酱醋往往糅杂成难以下咽的糟糠。
家中开支紧俏,我每每假意夸赞,强撑果腹。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许青荷在背后出谋划策。
她说,若是逼得郡主娘娘吃不下饭,她迟早露出马脚。
我知晓江云淮的皮囊之下埋藏绵里藏针的算计,温柔情深的做派背后是自以为透析一切的轻蔑傲然。
可是我还是想听听他的解释。
我站在门前,嗓音沙哑,难免颤抖:「云淮,我没买成药,可是你的病好像已经好了。」
江云淮演技拙劣,并不高明。
他深知我待他如珠似玉,决计不会眼睁睁看着他旧症复发。
于是,他连自己的药程也记不清了。
明明应当饱受断药后咳血之苦的人如今却好端端立在我跟前。
被我戳穿的江云淮怔愣一瞬。
随后,他状似不经意将那碗清粥小菜打翻在地。
6
我低头瞧他慌忙收拾一地渣滓。
江云淮不敢面对我,理由却想得很快:「郎中不是说过,服药七年就能好转。」
他蹲在地上,不嫌粥米染污下摆,朝我微微一笑:「多亏娘子买药照看,我才能好起来了。」
「鹊娘,你真是我的福星。」
可我却始终笑不出来。
昨夜此处燃尽千金银炭,下人三五成群,衣冠锦绣。
如今他却随意拿我一针一线厘出的蔬米饭餐扣在地上,只作心虚的掩饰。
脸上的泪痕干了又湿,我声音哽咽:「江云淮,我从未骗过你。」
「我是清河县的孤女,父母双亡,出身低微,我本打算自梳独活。」
「成婚当日,你说你与我同病相怜,我们从此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我信守承诺,那你呢?」
我一脸郑重,神情悲苦。
江云淮似有触动。
我的夫君缓缓站起来,将我拢入怀中:「鹊娘,你在说什么傻话?」
「我江云淮此生一妻不相离,决计不会背弃诺言。」
可是他不加遮掩地挂在腰间的侯府玉牌硌得我好疼,疼得我的泪珠落在地上的碎瓷。
「江云淮,和离吧。」
我毫不犹豫地推开自作多情的江云淮。
他尚且错愕,我眼睫挂着泪,却伸手向他:「还回我的钱银,滚出我的屋子。」
7
「你是高高在上的侯爷,而我是一无所有的孤女。纵使我是卑贱之躯,可我也不容得侯爷这般戏弄。」
「我并非侯爷所期待的郡主,从此侯爷不必舍弃荣华,与我逢场作戏。」
那日,江云淮终于撕开他的假面。
我的夫君探究地看我一眼,他见我不似玩笑。
江云淮蓦然揶揄冷笑:「鹊娘,怎么不玩了?」
「你以为先恼羞成怒就占理了?如果不是你的那对假爹娘挟恩图报,非要逼我娶你,我何必自降身份和你虚与委蛇!」
江云淮的冷笑像淬毒的冰锥,狠狠扎进我心口。
「挟恩图报?」
我望着他,眼前却浮现爹娘浑身是血倒在门前的模样。
我很少去回忆,就仿佛爹娘惨死的那段岁月彻底沉没遗忘。
因为只有如此,才不会陷进痛苦的泥淖。
可是江云淮再次强迫我想起春日里,小侯爷一人一马快意进山游玩,却惹上山匪。
他一人不敌,浑身是血地闯进我家。
我爹娘拼死引走跟随其后的山匪,是我用瘦弱的肩膀扛他进柴堆藏好。
娘亲在临终之际攥着他的手,气若游丝地求他护好鹊娘。
他当时跪在血泊里发誓:「此生必不负她。」
原来,他一直以为是我算计了他。
是我不惜以人命性命做局,只为与华贵的公子在乡野间逢场作戏。
所以婚后这些年,他看似温柔体贴。
实则无时无刻不在等着看我原形毕露,等着我这位郡主玩腻了这贫贱夫妻的唱词,主动撕下伪装。
「你以为是我设计一切?」
我声音抖得厉害,雨水顺着发梢滴落,像永远流不尽的泪:「江云淮,我与爹娘只是山里的砍柴人,凭什么能设计你这位贵人?」
他眼神有一瞬闪烁,旋即又被厌恶覆盖:「谁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的身份,联合那对老货…」
「啪!」
我用尽全身力气扇了他一掌,手心震得发麻。
他愣住,难以置信地摸着脸。
「这一掌,替我爹娘打的。」我退后一步,指着门外:「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