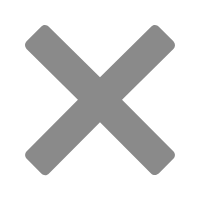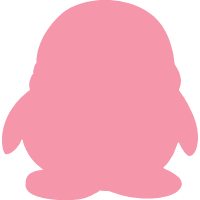-
他说娶我只是为了当摆件,我消失了他却疯了
本书由智阅文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01
我是谢临被下了药,欲火难耐时,
误打误撞闯进他房间的解药。
一夜缠绵后,
我成了谢临豢养的金丝雀。
他英俊多金,出手阔绰,
是京北有名的贵公子。
除了需要时才想起我这个妻子以外,
挑不出任何毛病。
在我自欺欺人,
只要觉得够乖就能留住他时。
在某个他醉酒的深夜,
我像往常准备接他回家,
却听到他和朋友闲聊:
“许星澜?娶她只是因为她够贱又够安分,是个很好的床伴而已。”
看着他领口不属于我的口红印,
我骤然清明,
原来我从不是他的港湾,而是他睡够了别人时,
一个不用费心应付的歇脚地。
第一章
酒杯摔在地板上的声音让包厢瞬间安静。有人开口打圆场:
“谢哥,哄哄嫂子,玩笑过了。”
谢临像没听见。他没看我,弹了弹烟灰。
一股冰冷的刺痛感从心口窜上来。我站起来:“回家。”
他终于抬眼,目光扫过我却没停留:
“我约了人谈事,今晚不回市中心的别墅,”
他语气平淡,“不必等。”
市中心别墅。那个镀金的笼子。我冷笑:“谢临,没人等你。”
转身,拉开门,走出去。门在我身后合上,但里面的声音还是挤了出来。
谢临带着轻蔑嗤笑:“你喜欢?那转让给你,反正摆哪都是摆。”
紧接着是哄堂大笑。像针扎在麻木的神经上。
我脚步没停,指尖却下意识按在锁骨下方。
一个凹痕,不是吻痕,是他某次粗暴拉扯留下的淤青。指腹下的皮肤仿佛还记着当时的疼。
回忆涌上来。
每一次都是这样。他从没温柔过。像完成一项冰冷的义务。
身体靠近,气息却是冷的,即使在失控的边缘,那双眼里也没有温度,
只有冷漠和……厌恶。
事后,他总是带着那种嘲讽看我:
“许星澜,你嫁进来,不就图谢家的资源和光环?装什么清高?”
或者更直接:“满意了?记住你的本分。”
每一次都像钝刀子割心。
车子开进那座灯火通明却死寂的家。空旷得吓人。
我直奔浴室,打开浴缸,放满热水。蒸汽模糊了镜子。
镜子里身体苍白,锁骨下的淤青在雾气里格外刺眼。
我拿起丝瓜络,用力擦那片淤青周围的皮肤,想搓掉什么。
皮肤搓红了,淤青却像刻在骨头上,纹丝不动。更深的痛翻上来。
婚后我躺过两次手术台。每一次都像剜掉一块肉。
第一次,我求他:“留下吧……求你……”他站在门口,眼神冰冷:
“谢家的血脉不是你这种舞女能玷污的。别妄想用孩子绑住我。”
第二次他甚至没露面,只让助理送来支票和一句话:
“处理干净。”
舞女。在他和他的圈子里,京市大剧院的首席芭蕾舞者,不过是个舞女。
婚前他说得很清楚,
“娶你是需要门面,你需要谢家站稳脚跟。各取所需。别妄想感情,可笑。”
我抱着可悲的幻想。以为时间久了,总能焐热一点他的心。
以为足够安分,就能得到点不一样的东西。
直到今晚。
直到那句“转让给你,反正摆哪都是摆”。
直到那阵哄笑。
原来在他心里,我和别墅里的摆设没区别。都是摆件。
我停下擦洗。热水还在流,蒸汽弥漫,却不暖。我看着镜子里空洞的眼睛和锁骨上的伤痕。
我的幻想彻底粉碎了。连带着那点可悲的、赖以生存的微光,也熄灭了。
手机铃声在清晨六点尖锐地炸开,我还没完全清醒,就听见谢临冷硬的声音:
“两小时后,嘉德拍卖行见。”
没有问句,没有多余的字,像在给下属下达指令。
我“嗯”了一声,听筒里立刻传来忙音。
这种麻木的服从,已经刻进骨子里了。
起身换衣服时,指尖扫过衣柜里那条没穿过的米白色裙子,
推掉了那场筹备了半个月的聚会,就因为谢临前一天说“周末陪你去看展”,结果到了当天,他只发了条短信:“天阴,没心情,不去了。”
梳妆台上放着个小本子,记着谢临的喜好:咖啡要手冲,三分糖不加奶;衬衫必须熨烫平整,袖口扣要纯银的......
可他连我芒果严重过敏都能一次次忘记。
有次家宴,佣人端上芒果慕斯,他还笑着往我盘里夹:
“你不是爱吃甜的?尝尝这个。”
我只能低声说“我过敏”,他却皱眉:“事儿真多。”
第二章
思绪扯回来时,我已经站在了拍卖行门口。时间刚好,不多一分,不少一秒。
这是他教我的,永远不能让他等。
谢临靠在沙发上,指尖夹着支没点燃的烟,眼底有明显的倦色,大概又是应酬到深夜。
见我进来,他抬了抬下巴,示意茶几上的拍卖图录:“挑一件,算补昨晚。”
“补昨晚”三个字像针,轻轻刺了我一下。
我拿起图录,翻页的手指顿住,里面一条蓝宝石项链的款式,和蜜月时我看中的那条几乎一模一样。
去年蜜月,我本来计划去维也纳,去看金色大厅的芭蕾舞剧,他却在出发前一天突然说:
“有个商业并购案要处理,回去。”
我攥着机票求情,他只说“正事要紧”。
后来在庆功宴上,我看到那条设计师孤品项链,小声说“真好看”,
他却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项链摘下来递给合作方的女伴,语气里满是轻蔑:
“许星澜,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就像这条链子,在我眼里只值它该有的价码。”
那时我还没醒,只觉得委屈,现在想来,那不过是他把我当摆件的又一个证明。
我合上图录,轻轻放在茶几上:“不必了。”
谢临的目光扫过来,带着点意外。
“那项链我本也不喜欢,就像我对你,曾经或许有过期待,现在,彻底算了。”
说完我转身就走,手腕却突然被一股蛮力攥住。
谢临的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我的骨头,我疼得倒吸一口凉气,回头看见他眼神阴鸷,
“许星澜,别他妈不识抬举!”
“这礼物是我赏你的,不是你来挑的。”他的手指越收越紧,
“摆清自己的位置,你配吗?”
我用力甩开他的手,手腕上立刻红了一片,疼得发麻。
但心里的那股劲却上来了,压了这么久的话,终于冲破喉咙:“谢临,我受够了。”
“上次舞团的重要排练,你一个电话说要陪客户,我就得立刻中断”;
“去年跨年演出,你说需要女伴撑场面,我推掉了准备半年的独舞”;
“我两次躺在手术台上,你连面都不愿露;你把我的尊严踩在脚下,把我当摆设,当床伴……”
我的声音没抖,只是眼眶有点热,
“当初答应联姻,是我愚蠢。我们离婚吧。”
谢临的面部肌肉猛地抽搐了一下,像是没料到我会说出“离婚”两个字。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嘴角慢慢勾起一抹冰冷的嘲弄:“好。非常好。”
“我求之不得。”他嗤笑一声,“你倒先说了?许星澜,我终于能摆脱你这块木头了。”
我看着他眼底的厌恶,突然觉得轻松了。
原来放下那点可悲的幻想后,心里会这么敞亮。
我扯了扯嘴角,声音平静:“那算是同喜了。”
说完,我没再看他一眼,拉开包厢的门走了出去。
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来落在我发红的手腕上,竟没有那么疼了。
第三章
后来一段时间,我几乎是泡在舞团的排练厅里。
《天鹅湖》复排的强度压得人喘不过气,直到深夜才能拖着酸痛的腿离开。
谢临搬的消息,还是舞团前台小姑娘闲聊时提了句,我才恍惚想起这个人。
倒不是刻意忘记,是真的没时间,沾床就能睡着的疲惫里,哪还有空隙装下他。
这天排练间隙,我刚拧开矿泉水瓶,手机震了震。屏幕上“谢临”两个字刺得人眼疼,
短信内容更荒唐:“刚结束董事会,煲个雪蛤汤,晚上我回市中心的别墅喝。”
我盯着屏幕,简直要被这理所当然的语气气笑。手指划过屏幕,直接拨了回去。
“谢临,你是不是没睡醒?”我靠在排练厅的把杆上,没半分软意,
“离婚协议还压在我抽屉里没签,你就急着拿前夫的身份来压榨我?
“要喝汤自己找佣人,或者......”我顿了顿,加重语气,
“带上你的协议,来舞团找我签字,咱们一刀两断,谁也别耽误谁。”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只有隐约的电流声。
然后,忙音突兀地响起。
我看着暗下去的屏幕,转身继续练舞。
当天晚上,我回了趟市中心的别墅,有些舞鞋和演出服还落在这。
推开门时,客厅里的灯亮着,茶几上却摆着份签好字的离婚协议,
谢临的名字签得龙飞凤舞,和他平时签文件的笔迹一模一样。
我走过去翻了翻,条款清晰,无子女,无共同财产分割......
这套别墅本就是谢家的,我婚前在老城区有套小公寓,早就搬空了私人物品。
再看房间,衣帽间里他的西装、浴室里他的剃须刀......
连书房里那盆他养的兰草,都没了踪影。
走得真干净。
我拿起协议,竟有种卸下枷锁的轻松。签上自己的名字时,没半点犹豫。
从今天起,我是许星澜,京市大剧院的芭蕾首席,不是谁的金丝雀,更不是谁的摆件。
刚把协议折好放进包里,手机就疯响起来,是我妈。
“星澜!你跟谢临到底怎么回事?”电话里我妈的声音带着哭腔,
“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你们离了,还说……还说你在舞团跟个有妇之夫不清不楚,是你先对不起他?”
“轰”的一声,我脑子像被重锤砸了下,手里的包“啪”地掉在地上。
“妈,你别听他胡说!我没有......”
话还没说完,手机又震了下,是谢临发来的彩信。
点开的瞬间,我浑身的血都凉了。
照片画质不算清晰,角度却刁钻得可怕。
第一张是我和陈默老师在后台,他正帮我调整白天鹅的手臂弧度,头微微低着,
照片只截了我们靠近的上半身,看起来像两人在依偎。
第二张更过分,陈默老师递给我一瓶水,指尖不小心碰到我的手,拍摄者故意把背景裁掉,只剩我们两人的手交叠的画面。
陈默是舞团的艺术总监,业界泰斗,孩子都上高中了,平时待我像亲女儿,帮我抠动作是常事。
可这些照片,经这么一剪,全变了味。
谢临的附言跟着跳出来:
“照片已发你爸妈,还有你几个叔伯。很快全京城都会知道,‘云裳’首席为了上位,勾引有妇之夫。”
“哦对了,当时你还是我谢临的妻子。”
我握着手机,指节捏得发白,牙齿咬得腮帮子发疼。
他不光要污蔑我,还要毁了我的名声,断我的路。
正想回信息骂他,手机又响了,是闺蜜苏棠,电话里她的声音急得快破音:
“星澜!你快看热搜!出事了!你上头条了!”
我颤抖着手打开热搜,心脏像被攥住。
【芭蕾首席许星澜插足恩师婚姻,道德败坏】
【谢氏总裁谢临惨遭背叛,商业联姻破裂内幕曝光】
标题一个比一个刺眼,点进去,评论区早已炸开了锅。
“原来之前说的舞女还真没冤枉她,本性难移啊!”
“我上周刚买了‘云裳’的演出票,现在觉得恶心,能退钱吗?”
“这种人怎么配当首席?赶紧开除!别脏了芭蕾这行!”
“潜规则,这女的烂透了!”
所有评论都在骂我,热搜标题里只标了我的名字,
谢临的名字被模糊成“谢氏总裁”,陈默老师的名字更是只字未提。
明摆着,谢临就是要把所有脏水泼在我身上,让我身败名裂。
手机不断弹出朋友的微信,有真关心的,更多是来看热闹的。
我深吸一口气,捡起地上的包,拉开门就往外走。
小区里有人认出我,指指点点的声音飘进耳朵:
“看,就是她,那个出轨的芭蕾演员。”
“长得人模人样,心思这么坏。”
我没回头,也没辩解,只是攥紧了包带,脚步不停地往谢氏总部走。
谢临,你既然敢做,就别怕我当面跟你算这笔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