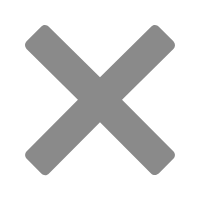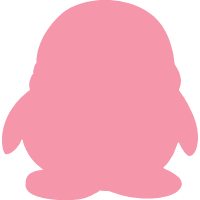010——魔发.樱花.木头人
回到家里。
餐桌上摆着四菜一汤,早已没有了热气。
但是妈妈亲手做的,只凭这一点,便让我心中充满了欢乐。
妈妈不在一楼,经由转梯我上了阁楼,阁楼的露天大阳台装修成了阳光房。
不出意外,我看到了妈妈。
也看到了那颗樱树,一夜之间,那颗樱树竟然开满了雪白色的樱花。
樱树下有一张简单而精致的圆木桌,三张藤椅,妈妈就坐在其中一张藤椅上,抬头静静地看着满树如雪的樱花,那条又黑又长又漂亮的大辫子静静地垂悬在她的脑后。
妈妈那根辫子从我的记忆开始,就一直散发着一股无穷而又诡异的迷人魅力,华丽如同柔美的梦魇,一直缠绕着我不曾散去。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很想去摸摸那根辫子,触摸那上面属于妈妈的味道和温暖。
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妈妈爱自己的头发,胜过爱我。
也可以说,妈妈根本就不曾爱过我。
她爱的只是那个男人,她那根辫子也只是为那个男人而留的。
从小到大,她一直都不过只是把我当作发泄的对象,当作是自己不禁意时捡到的一个工具,可有可无罢了。
还记得有一夜,我趁妈妈睡着了,偷偷去抚摩她的辫子,她突然惊醒,二话没说,随手便狠狠地给了我一个大耳瓜子。
怒不可扼地朝我咆哮道:“谁让你摸我的头发的,谁让你摸我的头发的,谁让你摸我的头发的,你凭什么摸我的头发,你跟你那个该死的男人一样,都是骗子,都是贱货,都该死,都该下十八层地狱,都该永世不得超生,我的头发不是给你摸的,不是给你摸的,不是给你摸的,不是给你摸的……”
说着,说着,妈妈便哭了,然后跪在床上,双手抱紧自己,全身都在剧烈地颤抖着,凄凄呢喃:“不是给你摸的,不是给你摸的,不是给你摸的……”
她一边说,一边拼命而疯狂地蹂躏着自己的头发,直到一根漂亮的大辫子被胡乱拆掉,蓬头垢面,疯疯癫癫。
累了,发泄够了,妈妈才会停止她的歇斯底里。
我当时没有动,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她从癫狂到渐渐安静下来,看着她那空洞、麻木、没有丝毫神采的眼睛,看着她变成个完全没有生命气息的悲伤雕像。
然后我会拿过一把木梳子,轻轻地站在她的身旁,开始帮她梳头,一下一下的。
每梳一下,妈妈都会默默掉下一滴眼泪,我不知道妈妈掉过多少眼泪,因为太多,数不过来。
直到完全梳顺畅,然后小心翼翼地编织成一根又长又黑又漂亮的大辫子。
暗暗深呼吸。
我知道,妈妈最是喜爱白色的樱花了。
可是樱花是见风就落的柔弱花儿,风一吹,就在一夜之间全都凋谢了,翩跹如同伤势的雪花,温柔而又酸楚地漫天漫地,沉沦而永恒。
我经常看到妈妈坐在樱树下的藤椅上,抬头静静地看着樱树,她的手中有时会抓着一把樱花花瓣、或者别的花瓣,机械地放一片在嘴里,细细而又盲目地嚼咀着。
那一刻,她的气息总是倦怠而又凄凉的,犹如一团飘渺而又虚无的雪雾,近在眼前,似乎伸手便可触及,然而,当你伸手过去的时候,却只留下一手的冰泪。
有时候,她又残酷而充满恨意的蹂躏着手中那些洁净而美丽的花瓣,直到汁液从她的手指缝间流渗出来。
像雨滴,像眼泪,像鲜血,滴落在她的裙子上,腿上,绽放成一朵朵凄美的花儿。
妈妈总是喜欢摧残这些细微柔弱的生命,甚至是我的生命,以及她自己的生命。
妈妈对这世间的一切生命都怀有一种莫名而深沉的恨意。
如果可以,如果有这个能力,妈妈会把这个世间、这个天地都翻个个儿。
妈妈会把这世间一切拥有生命的事物都给蹂躏而毁灭。
然而,生命是值得尊崇的,生命是奇特的,生命是伟大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生命又是变数的,无常的,脆弱的,渺小的,容易过去的。
可是生命对于妈妈来说,似乎毫无意义,只是一个错落而又可悲的笑话,只是一场无足轻重的梦。
梦还没有做完,就已经注定了结局。
眼睛睁开的那一刹那,就已经搓骨扬灰,灰飞湮灭,消逝无影。
我知道妈妈一直都在等待,等待那个男人回来。
可是那个男人不会回来了,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然而,她依旧自欺欺人。
在怨欲和绝望中沉沦,自毁,陷入沼泽,堕入地狱。
也许罪孽深重,也许罪无可赦,也许罪该万死。
她在无尽的需索和等待中,终究摆渡掉了自己充满美好而又罪恶的青春与才智。
不甘,执着与绝望,灵魂的寂寞与漂泊,索取不得。
却不知生命艳丽而又充满缺陷,却不知生命原本就是一个空虚的轮回。
与时间和宿命相搏击抗衡,最终一败涂地的,只是她自己。
妈妈的一切都恍若一场梦,一场真实沦陷进虚无之中的梦,而我却也身在其中,无法自拔,无法醒来。
在那个梦里,妈妈终究还是将自己送进了绝地,头也不回,义无反顾。
我缓缓抬头,望向天空,夕阳完全沉落,天地陷入昏沉之中,不见星月,只有那无尽的昏暗和沉重,笼罩天地。
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生命,来自宿命的缔结,残酷和决绝,促使我早已窥到了人情的淡薄和冷暖。
我再也不是个孩子了,可是,我多么希望我只是一个孩子,可以跟妈妈撒娇,可以跟妈妈哭闹,可以跟妈妈需索我想要的一切。
可是,我不敢。
也许,我也不配。
我只有我自己,妈妈曾经对我说过,这世间除了你自己,没有人会真的在意你、爱你,所以,你不要奢求我对你的爱,我早已不会爱了,也没有爱了,只有你自己才能好好爱你自己。
不知何时,一滴眼泪悄然滑落,沿着我脸上的面具流淌到我的嘴角,有一种浅淡而酸涩的咸味。
我悄无声息的擦去眼泪。
哭泣是懦夫的行为,眼泪则是弱者的产物。
这一生,我再也不做懦夫,再也不做弱者。
暗暗深呼吸,我轻轻走到阳台,站在那颗开满白色樱花的樱树下,站在妈妈的身旁,我柔声呼唤道:“妈妈。”
妈妈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静默如雕塑,不知道她到底在想什么。
不过我很意外,这一次她竟然没有蹂躏那些美丽而柔弱的花儿。
气氛压抑而沉重,我感觉有些难受和不适,再次唤道:“妈妈,吃饭吧。”
妈妈依然不理会我,好像我只是空气。
我早已习惯了她对我的无视和冷漠,不禁意间,我瞥了她对面藤椅上的男子一眼,心中猛地腾起一股浓烈的怨恨和愤怒。
虽然他穿着昂贵而华丽的衣裳,虽然他看起来和活人无异,但是他不过是个没有灵魂的木雕,从我记忆伊始,他就存在,是妈妈亲手雕刻的。
妈妈孤独的生下我,并没有找再别的男人,因为妈妈爱他,爱到了骨子里和灵魂里。
妈妈找不到他,想他想得发疯发癫,没有办法,便雕刻了一个他。
这个没有生命和灵魂的木雕男人,再也没有离开过她,时时刻刻都陪伴在她的身边,也将一直陪伴她到死。
然而在她的心里,一个没有生命和灵魂的雕像,却远远要比我重要。
她对这个雕像的付出和感情,远远要比对我这个儿子所付出的多和深。
所以我心中对于这个雕像,以及这个男人,时常充满了嫉妒和怨恨。
很多时候,我都想找个机会焚烧了他,毁灭了他。
只是等我渐渐长大,我慢慢才明白,妈妈之所以能一直活着,一直坚持下来,依靠的就是这个雕像,这个雕像完全成为了她活下去的动力和支柱。
如果我毁灭了它,就等同于毁灭了她。
不管她要干什么,只要她活着就好。
我只要她活着,哪怕是痛苦的活着,哪怕活得生不如死。
我知道我这样很自私,很残酷,可是,没有她,我不知道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暗暗深呼吸,收敛了心神,我再次柔声唤道:“妈妈,菜早就冷了,我们下去吃饭吧。”
一声轻叹,幽幽传来,妈妈终于有了反应,但她依然不动,也不看我一眼,只是冷冷地没有任何感情的问道:“你干什么去了?”
“我出去走了走。”
“哦。”她的声音轻飘而虚无,再也没有了下文。
我很想和她多说点什么,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静立一旁,默默等候。
“你去吃饭吧。”她淡淡道:“我不饿。”
稍作停顿,她看向对面藤椅上端坐着的木雕的男人,柔声笑道:“苏忞,你饿了吗?”
木雕的男人自然无法回答,只是保持着他的沉默和死寂。
此情此景,我早已习惯,但我心中仍然很不舒服,从小到大,妈妈几乎从未对我这般温柔和关切过。
胸中有怒火缓缓燃烧,即将呈现燎原之势,我微微蹙眉,双拳缓缓握紧,尽力地压抑和控制着不让自己当场爆发。
妈妈对着木雕的男人,自言自语道:“你也不饿啊,那就算了,我正好在这里陪你赏花谈天。”
木雕的男人依然沉默不语。
妈妈继续自言自语道:“苏忞,你看,这樱花多美,你总说你想去日本看樱花雨,等闲暇下来,我陪你去便是了。”
我终究还是没能彻底忍耐。
暗暗深呼吸,我轻轻道:“妈妈,他不是他,他是死的,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