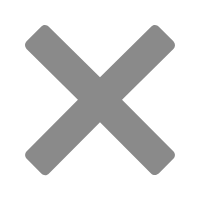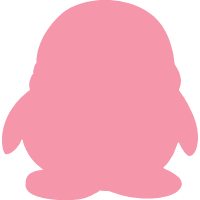016——我只是个木雕师,我不是女娲
慕幽香瞪大了眼睛,直直地盯着黑蛇,眼中尽是震惊和恐惧。
原来,她也会害怕。
我很想对她说,不怕,但我的嘴巴动不了。
杀死了黑熊的黑蛇一动不动地盯着死去的黑熊,血红的眼睛,残酷而又诡异。
然后他抬起了右手,将手中沾满鲜血的匕首直接刺向自己的心脏。
慕幽香急忙捂住自己的嘴巴,不让自己尖叫出声来。
刃尖已经没入皮肉,有鲜血溢出,只要继续深入,刺穿心脏,他也会死去,死在自己的手里,然后这一场危机便会就此打住。
突然传来狂暴地砸门声,有人怒吼道:“开门,快开门,快开门……”
眼看着匕首已经有一寸没入了黑蛇的胸膛之中,他双眼中的血色却急速退去,消散,他猛然清醒过来,瞬息的呆愣后看着地上满身鲜血、早已死去的黑熊,爆发出一声凄厉而又癫狂的哀嚎。
他猛然拔出胸膛里面的匕首,转身死死地瞪着我,悲哀而又绝望道:“你这个恶魔,你这个疯子,你让我杀了我的兄弟,好,我不杀你,我要当着你的面杀了你的女人给他们陪葬,我要让你一辈子痛苦。”
他忍着胸口的剧痛,握紧鲜血淋淋的匕首,一步一步地逼近了慕幽香。
慕幽香已经被吓呆了,忘记了任何动作和反应。
那冰封着我的阴寒之气瞬间破碎消散,我体内的力量也被一抽而空,眼看着他已经逼近了慕幽香,我双目瞬间充血,失声狂吼道:“香儿,跑啊。”
与此同时,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支撑着我狂扑过去,我一头撞向黑蛇,他身形不稳,直接将我的妈妈给撞翻在地上。
我怒吼道:“妈妈。”
妈妈倒在地上,依然不说话,只是冷冷地盯着我。
所幸,慕幽香已经清醒过来,她冷冷地盯着正在向自己逼近的黑蛇。
凌乱的脚步声传来,有人怒吼道:“我们是警察,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放下武器投降。”
我们国家的警察,每逢大事总是来得比较晚的,他们一般都是最后来收尸的,不过,这一次,他们来得还算准时,不管如何,我都该感激他们。
我倒趴在地上,浑身虚软乏力,再也无力挪动寸许,只能无比紧张和恐惧地盯着黑蛇和慕幽香。
而慕幽香与黑蛇相距不过一米,如果黑蛇真的不计后果要杀慕幽香,即便不能得手,慕幽香恐怕也会受到伤害。
不过,他却放弃了,缓缓地举起了双手,右手五指张开,那柄鲜血淋淋的匕首随之坠落在地山,乒砰作响。
我暗暗松缓了一口气。
黑蛇缓缓转身,看向我,神色淡然而又平静,他朝我笑了笑,笑得灿烂而又诡异,没来由的我却感到一阵心悸和恐惧。
我猛然瞪大眼睛,因为我突然想到了他左手之中那个黑色小遥控。
果然,他的左手拇指已经按在黑色按钮之上,然后他张开嘴巴,朝我做了一个口型。
我似乎听到了一声砰的剧烈的爆炸。
我失声尖叫道:“炸弹,香儿,跑。”
他笑了笑,正要按下了遥控器上的黑色按钮。
砰砰——两声枪声几乎同时响起。
黑蛇缓缓地倒在了地上,眼睛依然睁着,却带着不甘和怨毒。
有红白物自他的左脑脑门汩汩而出,他左手整个大拇指都彻底的消失不见。
那黑色小遥控摔落在地上。
我笑了笑,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整个人都彻底的瘫软在地上。
醒过神来的慕幽香快步过来,将我从地上扶起来。
我朝她笑了笑,她也朝我笑了笑。
那一刻,我很想紧紧地抱着她,但我不敢。
有荷枪实弹的特警上前将我们护在其中,有拆弹的专家上前拆除那些捆绑在我的妈妈、和那个木雕的男人的身上的雷管,有人处理黑蛇和黑熊的尸体。
总之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而指挥这一切的都是钟队。
黑蛇脑门上的那一枪也是钟队开的,另一枪是另一个特警开的。
钟队凝视着我的眼睛,幽幽叹道:“我说过每一次碰到你,都不会有什么好事。”
我冷冷道:“那我们这相见,一定是您口中所说的必然,而绝非偶然。”
钟队微微皱眉,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对左右荷枪实弹的特警吩咐道:“先带他们下去。”
“是。”那两名特警便要带我和慕幽香下去。
我盯着钟队,冷冷道:“我要去看看我的妈妈。”
钟队神色复杂的看了我一眼,淡淡道:“拆弹专家还没有完全解除安全隐患。”
就在这时候,拆弹专家过来报告:“钟队,电雷管已经拆除,房屋也已经进行了安全排查,确认安全无虞。”
钟队眉头紧皱,眼中闪过一抹不悦和恼怒,但还是点了点头。
拆弹专家带着属下离开,只是临走前却满脸狐疑和不解地瞥了我一眼,那一眼似有深意,想来他已经发现了。
稍作沉吟,我凝盯着钟队那双阴蛰而幽深的眼睛,轻轻道:“现在我可以去看看我的妈妈了吗?”
“可以。”他回答的很干脆。
我已经恢复了些许力气,在慕幽香的搀扶下,走向我的妈妈。
在经过钟队的身边的时候,钟队突然轻声叹道:“死者已矣,何苦执迷不悟,这样下去,你的妈妈恐怕不得安宁,何不将一切放下?小苏,你还小,人生的路还很长,过去的早已过去,你该放眼将来,何不好好的去过自己的生活。以你的条件,你想干什么不可以?你很聪明,也很有潜质,假以时日,你会成为一个伟大得人。人,要好好为自己活着才对。”
他的话,字字如尖锥,每一个字都刺入了我的心脏,刺入了我的灵魂,刺得我千疮百孔,鲜血淋漓。
痛。
真的好痛。
痛得我全身都在剧烈地颤抖着。
张了张嘴巴,我怨恨无比地盯着他,不甘而又绝望道:“你胡说八道。”
钟队凝盯着我,神色间尽是怜悯和叹息,他柔声叹道:“其实你自己比我更清楚,梦早已碎了,你该清醒了,你已经快十六岁了,已经快成年了,总要学会面对现实,面对你自己。如果你还执迷不悟,总有一天,你真的会彻底的疯掉,会害死你自己。”
“滚。”我终于爆发,咆哮道:“这是我家,谁让你们进来的,全部给我滚。”
“那你自己好好想想。”钟队看着慕幽香,微微笑道:“麻烦你照顾好他,我们先下楼去,走吧,都下去。”
除了慕幽香,其他人都跟着钟队下楼去了。
我呆呆地看着已经被重新安坐在那颗樱花树下的藤椅上的妈妈。
妈妈依然不说话,只是一脸冷漠的看着我,好像我是她的敌人。
我突然感觉好累,好疲惫,腿一软,我直接跪在了地上,跪在了妈妈的面前。
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残酷,很多时候我会感到寒冷,一种从灵魂深处透散出来的极寒极冷,一点一点扩散到全身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胞,每一处骨髓。
我下意识的伸出双手抱紧自己,只是希望能给自己一点需索而又渴求不到的温暖,只是希望不受到外界的干扰和伤害。
可是,那来自这个丑恶的世界以及灵魂深处所带来的孤单和绝望,让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极恐极惧,无法压抑和克制。
我只能紧紧地拥抱着自己,给予自己温暖和保护,至于是被这个世界所排斥和拒绝,还是自己排斥和拒绝这个世界,并不重要,也无意义。
灵魂的干涸与枯萎,一如无根飘萍,被放逐荒漠,没有发芽和成长的机会。
所以我早就萎蔫而凋谢了。
我抬着头,痴痴的凝望着妈妈,多年来,我第一次流泪了,我的眼泪很快就打湿了我的脸上的面具,很快就模糊了我的视线。
妈妈,我好想你……第一次,我终于像个孩子一样,放声痛哭起来。
我不知道哭了多久,有一只纤嫩而柔软的手突然伸过来,轻轻地搭放在我的肩膀上,带给我一种深沉而又细腻的温暖。
我渐渐止住了哭声,缓缓转头,看着我左肩上面的纤纤玉手,看着慕幽香,看着她那张在梦幻中出现过无数次的绝美而又哀伤的脸。
“你都知道了?”我的声音嘶哑而无力。
她那双澄澈而清凉的眼中,闪过一抹温柔和悲伤,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笑了笑,自嘲而苦涩道:“那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疯子和神经病?”
她摇摇头,幽幽轻叹:“你只是太想、太爱你的妈妈了,这并没有错。”
我知道她说的是真话,感激道:“谢谢你。”
她笑了笑,浅淡而又温柔。
我转过头去,微微抬头,仰望着我的妈妈。
仰望着她那永远不变的容颜,她看起来虽是活的,但浑身冰凉而又坚硬,我始终感受不到她们的温暖。
因为她是死的,是假的,她跟那个木雕的男人一样,只是我雕刻出来的木头人。
妈妈因为太过思念、太过爱那个男人,从而亲手雕琢了他。
我因为太过思念、太过爱我的妈妈,所以我也亲手一笔一划的雕刻了她。
多年来,只要看到她,我便以为她还活着,还陪着我,永远都不会离我而去。
可是她早就死了,我早就成为了一个孤儿。
我什么都没有了。
一直以来,我都只是在自欺欺人,我一直以为,只要我骗着骗着,一直骗下去,她就会一直活着,一直陪伴着我。
却不知道,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她已经死了。
她只是木头人,即便我能给予她身体和神态,我也能够模仿她讲话,这几年来,我一直自说自话,但是我无法给予她血液、温度、生命以及灵魂。
我就算付出我的一切,也无法让她复生过来。
我只是个木雕师,我不是女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