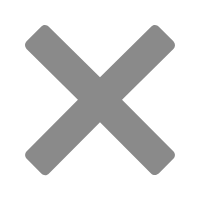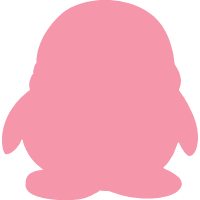第二章 绣鞋
一
东屋里,张大却是已经醒了过来。春杏进屋,坐在床边问他:“你妹妹身上有块胎记,你可还记得?”
张大酒方醒,头昏脑涨,便随口答道:“是啊,不过这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当年我爹还因她这胎记不喜她,才把她卖到相府做丫鬟呢。”
春杏心中狐疑,许是自己看错了也说不准,为了消除自己的顾虑,她还是决定亲自去看看。
清舒正在沐浴,门外忽然响起了敲门声。她本能地往水里一缩,问道:“谁呀?”
“妹妹,是我,我给你送身衣服进来。”
原来是春杏。清舒放下了警惕,轻轻道:“嫂嫂请进!”
春杏轻推开门,见梨木衣架上挂着清舒的衣服,衣服上系着一块通体碧绿的玉佩,一看就是贴身之物,她一个丫鬟,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东西?
清舒见她目光滞在那块玉佩上,猜到她的疑惑,忙道:“这是小姐赏的,小姐平素待人宽厚,待我也如姐妹一般,并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
春杏把一身布衣放下,走到清舒边上,清舒有些不自在,春杏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妹妹不愧是大户人家出来的,瞧这肌肤水嫩的,叫嫂嫂好生羡慕。”
春杏刻意抬起清舒的手来看,这一次她看清楚了,忙放下她的手出去了。
清舒疑惑,不知她是什么意思。
正屋里,张大嚷着要吃饭,春杏把饭菜热了端到桌上,语气带着明显的责备:“叫你别去赌了,你看看这个家都成什么样了,你爹留下的家业,就被你败得只剩下这几间破房子,你要是再赌,我就搬回娘家再也不回来了!”
张大一听急了,当年他娶春杏可是花了不少彩礼钱,要是她真走了,那怎么成?忙好言好语劝慰,指天发誓说自己再赌就不得好死。
春杏明知他这是违心之言,但心里还是有了几分安慰,毕竟他赌归赌,这些年其他什么事都是依着自己的。
“行了,吃完饭就去把园子里的菜浇一下,省得你一天到晚往外跑,没个正事。”
张大无不应允。吃过饭,正要往菜园子里去,瞥见厢房里一个妖娆的身影,以为自己眼花了,他揉了揉眼睛,凑近了些,听得里面水的声响,又想起春杏的话,心下也生了疑,把指沾湿,想捅破窗户纸看个究竟,门突然一开,他直直撞进门内,未及看清人影,背上已落下重重的板子。
张大没想到自己的妹妹是这么个狠角色,一边喊痛一边道:“秋棠,别打了,我是你哥哥!”
清舒的手顿住,“哥哥?”
春杏听见响声赶了来,见张大捂着后背,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冷眼扫过张大,“哼”了一声便走了。
张大急忙追了出去。
东屋里,春杏正在收拾衣服,张大赶忙上去赔礼道歉:“娘子,我……我不是故意的,你不能走啊!”
“让开!”春杏收拾了包袱,就往外去,张大急忙夺下她的包袱,一边承认自己错了,一边骂自己怎么不是东西,并保证绝不会有下次。
春杏坐回床上,哭道:“我嫁给你这么些年,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也就罢了,你惦记着外面的女人,我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你竟然把主意打到你妹妹身上去了,你心里还有我吗?”
张大看她气得不轻,跪在她面前,拉着她的手道:“娘子,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原谅我这一次,娘子!”说着竟是已经哭了起来。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我怎么就嫁了你这么个窝囊废?”说罢朝门外去了。
张大见她不走了,立刻收了眼泪,起身抹了把眼泪,把包袱放进衣柜,方去菜园子浇菜。
春杏去厨房端了碗饭来到厢房,闻屋中低泣声,春杏轻推开屋子,把碗放在桌上。清舒忙止了哭声,起身道:“嫂嫂怎么来了?”
春杏看了看她哭得红肿的眼睛,拉过她坐下道:“来,把这碗蛋汤吃了补补身子,你哥哥就那德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回头我替你收拾他。”
清舒反安慰她道:“嫂嫂,我没事,倒是你,让你受了委屈,是我们张家对不住你。”
春杏道:“哎,说什么对得住对不住的,这辈子嫁给你哥哥,我也认了,好在他还听我的话。”
张氏回来后,春杏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她。
张氏听了,一时急火攻心,气得又引发了旧疾,拿鸡毛掸子将张大打了出去,指着他骂道:“孽子,孽子啊,我是造了什么孽,会生出这样的儿子啊!咳咳!”
春杏忙为张氏缓气,朝张大使了个眼色,张大立刻跪下抱住张氏的腿道:“娘,我知道错了,您打我吧,您骂我吧,千万别气坏了身子!”
张氏一脚将他踹开,坐在一边咳着,脸色气得涨红。
“娘!”清舒一身白衣,碎发被风拂起,款款进门,越过张大来到张氏面前。
张氏见她,满眼心疼。清舒将药喂张氏喝下,张氏喝了药,重重叹了口气。
清舒回身将张大扶起,张大想起她打自己时的凶狠模样,身子微颤了颤,清舒此时却是无比温柔地将他扶起,柔声道:“哥哥快快请起,都是妹妹不好,不该失手打了哥哥。”
张大看着她柔顺的模样,一时失了神,春杏一把拉过他道:“还不快回屋去,别在这儿让娘看着心烦!”
这句话像是对张大说的,却又不经意地看向清舒,清舒心一惊,难道她看出什么了?
二
夜间,闻屋中翻箱倒柜之声,清舒悄然起身,随手抓起茶壶,朝那人走去,将茶壶向那人砸了过去,那人叫喊一声往院子里逃蹿去了。
她这屋子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唯有那块玉佩,而那块玉佩……
清舒猜到春杏对她起了疑,半夜来偷玉,不是张大又是谁?这是娘留给她唯一的东西,她一定要好好保住它。怕他们不肯死心,清舒心里顿时有了主意。
第二日,她打听到有个朱雀楼专卖假首饰,表面与真货无异,价钱也便宜。
她如今身无分文,还值些钱的,也就足上这双珍珠绣鞋了,这是奶娘亲手给她做的,娘虽疼她,但有大哥和小妹,她也不能时常顾到自己,倒是奶娘,对她比对秋棠还好些。
到街上,将珍珠绣鞋脱下拿在手中,清舒迟疑片刻,还是咬牙进了当铺。
“老板,你看看这个!”
当铺老板是个四十岁上下的男子,见清舒这般打扮,以为她只是当几件破衣服,没想到竟是一双珍珠绣鞋。
“一两银子,不当拿走!”
“一两?”平时要用的东西都是秋棠出来买,她并不知道市场物价,但这绣鞋绝不可能只值一两。
清舒拿了绣鞋转身就走,那老板忽然拦住她,清舒将绣鞋藏到身后,道:“怎么,我不当了,你还想明抢不成?”
老板嘿嘿一笑,“你一个穷苦百姓,哪儿来这么贵重的东西,我看这八成是你偷来的。”
老板朝伙计们使了个眼色,伙计们朝清舒围过去。
“你们,光天化日之下,还有王法吗?”清舒意识到自己遇到奸商了,退到门外,转身就跑,那伙人追了上来。
“站住别跑!”
清舒边跑边推倒沿途的杂物挡住他们,到一座楼前,忽然脚下一滑,身子向后一倾,直往地面倒去。正在这时,一抹白影从楼上飞下,将她拦腰接住。
这男子一身白衣,面容极美,一只手接住她,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折扇,气质温和。
站稳后,清舒忙从他怀中挣脱,欠身道:“多谢公子!”
“站住,看你往哪儿跑,给我抓住她!”
见他们追上来,清舒看向白衣男子,面露难色。
白衣男子手中折扇一张,挡在清舒面前,不慌不忙道:“这么多人这么追着一位姑娘,恐怕不合适吧?”
那老板上前扬眉道:“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来管我的事,也不打听打听我王老五是什么人。”
白衣男子轻笑道:“在下孤陋寡闻,还真没听过您的大名。”
老板卷起袖子,双手叉腰道:“那你可听好了,如今的县令王老二是我二哥,这姑娘偷了我店里的东西,我要捉她去县衙问罪。识相的给我滚开,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白衣男子仍是浅浅笑着,折扇一挥将老板震出几丈远,众人一慌,老板抹了鼻血阴狠道:“给我上!”
众伙计围了上来,白衣男子拉过清舒,躲闪之时一个回身,只见他手中折扇翻转,清舒不觉眼花,眨眼工夫,那几个伙计已倒在了地上。
老板见白衣男子如此厉害,心也慌了,爬起来道:“你,你给我等着!”说着带着一众伙计灰溜溜地离开。
百姓们见平时欺负他们的恶霸被打得这样惨,都在边上叫好。
白衣男子转身问:“姑娘没事吧?”
清舒摇头。
白衣男子从袖中取出一锭银子:“姑娘若是有什么难处,顾某这里还有些碎银子,姑娘先拿去用吧!”
清舒未接他的银子:“无功不受禄,公子若真想帮小女子,就买了我这双绣鞋吧!”
白衣男子这才注意到她手里的绣鞋及她光着的脚,夺过绣鞋塞入怀中的同时将她打横抱起,清舒扶上他的肩以免自己跌落,“哎,你放我下来!”
男子腾身一跃朝空中飞去,看着怀中的人儿笑道:“姑娘就不怕被人看了你的玉足?”
清舒虽还是个未经世事的少女,却也知道女子的脚是不能随意给人看的,娘说过,若是被男子看了脚,就要嫁给那名男子,思及此,清舒不禁红了脸颊。
到了一处空地,男子将她放下。这是一家酒楼,他们此刻是在楼顶。
“采萍,给这位姑娘拿双绣鞋来!”
一蓝衣女子道:“是!”片刻工夫,便拿来了一双绣鞋,比清舒这双还要精巧些,只是上面没有珍珠。
将清舒扶坐到一旁,男子即要替她穿鞋,清舒急忙夺过鞋子穿上,惶急起身,在离他半尺的地方向他行了一礼,“多谢公子!”
白衣男子冲采萍使了个眼色,采萍把银子给了清舒,清舒转身离开了酒楼。
男子看着慌忙逃去的女子,脸上浮起一抹笑意,把鞋子取出细细一看,鞋子还不及他的手掌大,绣鞋上,残留着淡淡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