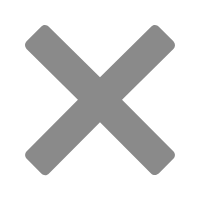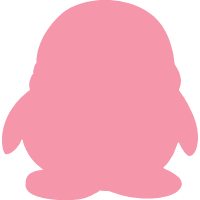对话
翠色丛新的时节,仍余些深冬凛冽的味道,澡桶里的水从热到凉,催着杜恒结束神游到不知何处的状态。他抖了个小小的寒颤跨出水桶,将所有能穿的衣服一件件穿在身上,从里到外,从厚到薄,出门寻人前还顺手拿了阿宝的手炉。这手炉原是七七从西沙黑市淘来给自己备的嫁妆,不是惯常金银铜的材质,而是木头制成,却不怕火烧水浸,放了碳火进去还能袅袅晕出些淡香。不想有一回阿宝大王去串门,见着这宝贝以后就离不开眼了。于是腆着一张小脸皮缠了七七许多日,又是端茶送水,又是嘘寒问暖,捶肩敲背,撒泼打滚,无所不尽能事,最后七七着实受不住阿宝成天睁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在她耳边念叨“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鹦鹉饶舌的行为,才转赠了阿宝。这手炉也因此成了三宝新晋的心头好,成天抱在怀里,杜恒想碰一下都不给。
今日却大喇喇地放在桌上,杜恒一厢情愿觉着这是贴心的阿宝特意留给他用的,拿的甚是心安理得。
杜恒在不候楼住下的这段时间,没干什么跟他读书人身份相称的正经事儿——日里不曾诵书,灯下不曾夜读,自诩是个君子却在庖厨进进出出,柴米油盐酱醋茶分得门清,生火开灶拍黄瓜做的得贼溜,没事干的时候就成日里在不候楼的地域范围内瞎游荡,也因此将阿五一日的行程摸了个八九不离十,这姑娘的日子过得实在是千篇一律。
杜恒到了二楼,就看见那扇凌空敞开的雕花门,门外是通往后园的悬索,阿五正垂着两只脚坐在门槛处。杜恒对那晚在风雨中飘荡的经历仍然心有余悸,又怕自己突然在阿五背后出身将她吓得一头栽下去,所以上了楼梯远远就开口:“阿五,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周遭无人,宜谈心呐。”
背对杜恒的阿五听见这一句开场白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早上杜恒哭哭啼啼要跟她诉苦的时候她就预感到今天落不了清净。杜恒这人看着已是弱冠,很多时候心性却跟阿宝大王一个样,拗着一股劲儿难缠得很。
她转过身,微微惊讶于杜恒胖了一圈的身量,开口道:“你这是?”
杜恒在距阿五大约七步远的距离端端正正地席地而坐,随口回道:“夜风太急,人间太冷,唯衣裳叠叠,可外抵严寒内暖心凉。”
阿五面无表情地转回头继续盯着她家楼主的住处,隔壁侯爷进了厅堂到现在还没出来:“说人话。”
“我认为咱得从前楼调点人手守后园,再不济整点防御机关也成,我发现这个世道上总是会有奇怪的人出没,不可不防。你是不是想知道肩不能提手不能扛的我今晨为何会出现在那高高的墙头上看旭日东升,来来来,我告诉你,我昨晚真是太惨了……”
“不想知道。”
“我昨晚在自己床上躺得四平八稳波澜不惊,睡姿甚是文雅,然而随着吱啦一声,房门被一只惨白的手推开,一个人影被凉凉的月光拉长映在屋内的地上……”
“说重点。”
“重点就是那人不请自来不问自进不由分说不容反抗地将我这么个老实本分尊法守度身羸体弱的书生从被窝里一把呼撸出来,拎着领子脚不着地上了墙头,用让人毛骨悚安汗毛直立的眼光威吓我许久逼良为娼般非要让我认他做叔父。虽说我确是个世上难寻,温良恭俭让的好孩子,但认亲可不是这么个认法。阿五,你说,长得聪明伶俐俊俏讨人喜欢也是一种错吗,我觉得我总是在背负我这个年纪不该有的烦恼。”杜恒发出了深沉的叹息。
阿五看着隔壁侯爷从厅里出来,距离太远瞧不清脸上的表情,看脚步却是轻快得很:“你认作叔父的那个男人,是不是一袭黑衣,脸上两撇八字胡,长的还挺好看?”
杜恒震惊:“你怎么知道?!莫不成此人还是个惯犯?!”
“知道什么,知道你架不住威逼认了亲还是知道你叔父的长相?”
杜恒抱紧自己,偷偷往后挪了一点距离,轻飘飘地回道:“都是。”
“以你如此能屈能伸的性格,不认这门飞来横亲才不正常。且我不仅知道那人的长相,还知道他是谁。”阿五一直是个惜字如金的姑娘,如今破天荒地跟上了杜恒絮絮叨叨的语言风格:“天子近臣,朝堂巨擘,军侯一品,四海名将,少年,这么个堂堂大佬,上赶着攀关系的人怕是能从咱这排到青州府去。到了你这却成了奇怪的人。”
杜恒倒吸一口冷气,抱紧怀里的手炉开始结巴:“这…这这…名头…听着…有…有点…响亮。普…普天之…下…下,能…”
阿五原先惜字如金,当下虽说受杜恒的刺激变得多言了些,然其本质上还是个干脆利落的姑娘,平生最受不住的便是跟结巴对话。所以她毫不犹豫地接了杜恒的话茬:“能与这四个形容一一对上的不过我朝不归侯一人而已。怎么样,是不是有种要走大运的激动感?”
“实不相瞒,我有种要倒大霉的不详感。”杜恒回神,“如不归侯那样浸淫朝堂识遍宦海浮沉旌旗招招不坠的人上人,一举一动辗转腾挪必是事出有因。我一介书生,身无长技,声名未露,也没什么可让人看上的,不是我,就是因为我周围的人。且这么锦衣夜行上门拎人,我瞅着这位侯爷原是想把我碾成渣渣眼不见为净,可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中途生硬改了主意,我两这才凑了对不情不愿无亲无故的叔侄,对了!就是外甥!为何是外甥不是义子?!为何这侯爷来我不候楼似进自己家中,如入无人之境?我知道了,这个传说中的侯爷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这是暗搓搓占我婶子的便宜啊!上了年纪的老男人,妻妾成群,还净耍些不入流的伎俩占良家女子的便宜,真不要脸。”
阿五闻言瞧了眼杜恒:“错了。”
杜恒咬牙切齿地问:“哪错了?”
“首先,不候楼这片地界当初是这位上了年纪的老男人置办下来的,除了他,没有不明身份的人可以在这里来去自如。其次,郢都的百姓都知道不归侯是个鳏夫,后院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