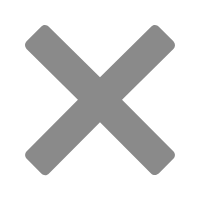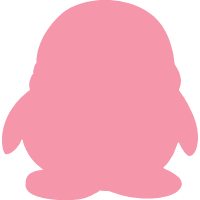静水流深
程顼原是天弘三十二年的状元出身,打马游街时,救下了因受惊吓而喘疾发作的相爷嫡孙女。这位孙小姐是出了名的才貌俱佳,只是生来带喘,病弱体娇,一来寻常人家高攀不起,高门朱户因着她的身体条件也鲜少求娶,二来许是文人多清高的缘故,兼之又有爷爷给的绝对婚嫁自择权,这位小姐自己也是个在嫁娶之事上极有主见拒了几桩求亲的人物,是以快过婚嫁之龄仍待字闺中。
娶亲一事,古来以情论事者少,图利借势者多。如相府这般的,实属天下少见。
说及此,不得不提一句,当时大楚的当朝丞相言机也是个妙人,本是年纪轻轻世家子,却行不管不顾情深事。原配发妻早早撒手人寰,身后独留一个幼子。当时满都蝇营狗苟的人家闻风而动,欲往这鳏寡孤独的香饽饽身边塞一个可心人。后来年轻的相爷实在烦透了明里暗里上门说媒的人,直接请了道不续弦不纳妾的圣旨供于厅堂之上,釜底抽薪绝了所有人的心思。他一个人将儿子言显抚养长大,言显也不曾辜负父亲那些年又当爹又当娘的付出,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娶妻生子,封疆为臣一样都不曾落下。
可惜好景不长,时值大楚国弱,境内不安,边线上又摩擦频起。言显夫妇在一次进京述职中被流寇所劫,命丧深山,只给相爷送回了一个尚在襁褓中吐泡泡的孙女。人到中年的相爷经历丧子之痛,万般无奈之下还得再一次扛起独自抚养孙女的大旗。他从不曾将男孩看得比女孩重些,只一视同仁,对这唯一的孙女珍之重之却也不曾过度溺爱,以无愧于养娃高手的外号养出了一个名满郢都的才女——言安安。
状元郎长街勒马伸手相救,言家安安一眼情深折衣而嫁,当年才子佳人一出戏,羡煞郢都上下。据说婚后两人琴瑟和鸣小日子过得甚是美满,但不过两年,战乱突起。大庸联合其他四国大举进犯,大楚节节败退,朝中已无可用之人。时任礼部侍郎的程顼出人意料于朝堂上列席而出,以一介文官之身临危受命领军抗敌。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大楚这是出昏招,离亡国不远了。不曾想这一场仗一打就是一年,程顼麾下楚军最终在泗水河畔以少胜多,大败五国,收复失地,还一手主导了泗水息战令的签订,才有六国相安的局面。至于其后三年间北陌、南陈、东汇各归西沙及楚、庸三国所有,则是后话了。
只是英雄凯旋归来,美人却已葬于坟冢。战时冬天那一场雪,言安安喘疾复发,终究是没熬过去,不曾留下一儿半女,不曾留下只言片语。程顼封侯当日,满朝文武对着老态龙钟的君王御座阶下长身玉立的男人俯首陈贺,唯独言相称病不出。及至不归侯顶着个鳏夫的名头不显山不露水地建了不候楼,后来又一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局外人态度强势扶立如今的天景帝,以帝师身份教新君雷霆手段革除积弊,一手缔造了如今这国富兵强的楚国,这位老人都再未见这孙女婿一面。
杜恒原是想找人倾诉一舒胸中闷气,不曾想听了阿五一席话,气郁更甚。他一会儿反省自己在人家的地盘上说人家的坏话这事儿做得不厚道,一会儿又气这不归侯欺世盗名,顶着良臣名将情深不娶的名声干着仗势欺人强买强卖的勾当。
世上许多事本不能深究,是非对错子丑寅卯,一旦掺了局中人的爱恨情仇,看客是再难断得清楚的。世人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可许多人不知道,此话源出观棋人之口,都是些观棋不语的君子。而所谓君子端方,说的是君子多清正自持,事不犯己者不置喙。杜恒走在熙熙攘攘飘着晨食香气的星罗街上,突然就想起了他那秀才养父曾与他说过的这番话。
杜恒小时候就是个活泼的性子,每每总能碰见些想不通的事,父亲便会带着他坐在村口槐树底下,两人一起看着官道上来来往往赶路的人与车马发呆,晴时有飞扬的尘沙,雨时有滴水的枝丫。待得明月上山头,或是微雨斜阳后,父亲的眼里会有星星点点疏阔辽远的笑意,会摸着他的头,揪着他的鼻子叮嘱他莫做冷清君子,做个红尘中摸爬滚打嬉笑自在的市井人就好。他从不为他实实在在地解惑,只是带着他在热闹的边缘发呆,跟他说些似是而非奇奇怪怪的悄悄话。他总怀疑父亲是因为解答不了那些光怪陆离的事,又有着“为父无所不能,不能在吾儿面前犯怂”这样匪夷所思的心理包袱,才常常忽悠他,以至于养成了他如今爱往热闹之地去,在素不相识的人群里放空自己的习惯,来来往往的过客脸上有这花花世界的众生百态,看多了,便觉压在心上的那点破事不是事了。
走过人群,杜恒不知不觉就出了城门,不远处便是大楚鼎鼎有名的离山。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离山脚下别君庭,是远行人孤身上路的起点。说是庭,其实不过是个四面透风的亭子罢了。杜恒握紧手炉穿过亭子上山,山顶有风猎猎。眺望远处,那一片巍峨高耸主色沉寂的建筑群,依稀是楚王宫的模样。杜恒欲再极目远眺,却不妨颈后挨了一记手刀,翻着白眼晕了过去。
远处的楚王宫内,水凝香袅袅。一局残棋,两人对坐。
“当初您使计引得羟国内乱,又孤身犯险去给西沙老王下了个古古怪怪的伏毒,破了五方联军,让楚国得以绝处逢生逆风翻盘。如今七年过去,昔日预设的局面都成了,西沙已散,大庸将乱,您待如何?”年少的声音自殿内响起,“将军,承让。”
“羟国内乱,可不是臣的功劳。陛下这一手偷车换将使得极好。可惜……呵,您的将军,臣的马儿这就背走了。”
“……”
远些的坊市角楼檐下,一高一矮两个人。
“这东西阴差阳错到手,是天意,如今那处一片浑噩,您若听之任之,就真成了无根之人。”
“那就,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