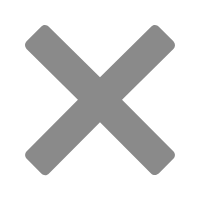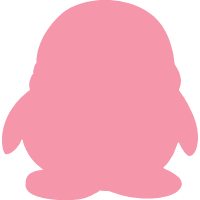第19章 第十九章
“梁友安,我是不是提醒过你,金翌的事情要低调高效?”蒋杰敲着桌子,气恼地质问,“现在奥斯康知道我们要抢人,都开始竞价了!你怎么就弄到要增加签约金预算的程度呢?”
“我本来想周一的时候再跟您汇报一下。”梁友安取出考察报告放在蒋杰的办公桌上,“关于金翌的长期约,我认为应该慎重考虑。”
“那是周一的事。”蒋杰看也没看,就把报告推开,“这两天你抓紧弄一份新的合约,金翌的名字我已经跟高总提过了,一个星期拿下来。”
跟上司提过的事就不能再改,哪怕明知有问题也不能。这种规矩,在格子间里工作过的人都懂。因为问题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暴雷,就算暴雷了锅也不一定落在自己头上。但提了的事没做到,就是现成落在自己头上的把柄。
懂归懂,也还是会觉得荒诞。
“好,我知道了。”梁友安说。
奥斯康并不是真的重视金翌,否则不至于合约都要到期了还迟迟不续。
等到易速和金翌接触,他们跳出来竞价,也不是真心舍不得这个潜力股,纯粹就是不想便宜了竞争对手。
竞价到一定程度,万一真拒了易速,奥斯康也未必舍得出这么高的价格接盘他。到时候金翌就真要鸡飞蛋打了。
梁友安觉着,以金翌的聪明,未必意识不到这一点。
拟好新合约之后,她照旧带上明宇,直接拉了一车装备到新翊。
联系好教练,等到下午训练一结束,就开始挨个分发,“这是我们易速代表翌哥,给大家送的运动装备。”
有免费的新球衣领,所有球员都兴高采烈地涌上去。
穿上衣服还不忘回头向金翌道谢,“翌哥,这衣服行啊!”
就只有宋三川把明宇塞过来的训练服和球鞋直接摔了回去,难以置信地看向梁友安。
梁友安避开他的目光,直接转向金翌,把新合同递过去,“新的合约里,签约金已经是我们能给出的最高上限了。这种赞助,按道理来说,本来仅局限于你本人。但是我们易速现在愿意以你的名义,无条件地支持你整队全年的装备。”
金翌很享受这种众星拱月的感觉,更喜欢看宋三川、梁友安这种得罪过他的硬茬子吃瘪、服软的模样。
面上已经流露出得意之色。
“其实经过这段时间跟你的接触,我能感觉得到,你还是非常在意你自己在队内的权威的,所以我们易速也愿意无条件地给你最大程度上的加持,”梁友安说,“不管是在训练、比赛,还是生活上。目的嘛,当然是为了让你打出更好的成绩。”
“呿,弄得这么大张旗鼓,我要是不答应的话,那就是不懂得顾全大局了呗。”
“这是双赢。”梁友安说,“毕竟只有你打出更好的成绩,我们易速才会更好,不是吗?”
金翌被她奉承得很是舒坦,终于伸出手来,“带笔了吗?合作愉快。”
领完了装备,队员们很快便勾肩搭背,兴高采烈的离开了训练场。
让明宇把合同带回去,梁友安则留下来,跟宋三川一道清理训练场。
向金翌服软,她自己其实无所谓。
成年人的世界,谁还没有个钱难赚屎难吃的时候?
情绪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制造问题。在成人的社会里,是最奢侈无用的东西。
但对宋三川这个率真而热烈的人而言,向金翌这种败类妥协,无疑是一种背叛吧。
在宋三川为了帮她出头,当众跟金翌翻脸之后。她当众的微笑妥协,当也格外令人感到厌恶吧。
“你这算什么?一对一帮扶吗?”她从宋三川手里截过球筐俯身开始捡球时,宋三川有些恼火。
“签约是我工作立场,不代表我个人的意愿。”
宋三川冷笑,“所以你在这儿捡球,是捡自己良心呢?”
“对。”梁友安说。
宋三川却越发恼火起来,“明白了!你们就像这些球一样呗,被装在轨道里,指哪儿打哪儿,落哪儿算哪儿,是吧?”
是,梁友安想——她为这份不能拥有自我意志的工作,对这个不能表达自我情绪的自己,感到厌恶透了。
。
这一天的训练,宋三川没有出现。
和金翌签约之后,这阵子,蒋杰那边的事务梁友安渐渐开始让yoyo接手,尽量腾出时间来羽毛球队这边照看。原本是为了找机会帮宋三川打开心结,宋三川却总是躲着她。从教练和其他球员这边打探到的消息,也很有限。实在有些难以入手。
正想着是不是该去假发店里找安从探探口风,就见安从从训练馆里走出来。
梁友安略一犹豫,连忙追上去,“安叔?”
安从果然还记得她,“小安?你不是在易速上班儿吗?怎么到这儿了?”
“最近公司刚好和这家羽毛球馆有合作,今天过来看看。”
“哦。”
“宋三川今天好像不在队里,您过来是?”
安从就叹了口气,“唉,我就是趁他不在才来的。这臭小子,闹着要退役呢!”
“退役?”
“嗯。退役申请都交了。之前也闹过几次,情绪缓过去也就算了。谁知道这回来真的了。这不我来找他教练,把申请表要回来嘛。”
梁友安沉默了片刻,“申请表您要回来,他还能再重新写。就算劝他坚持下去,也只是不痛不痒。”她看向安从,到底还是下定了决心,“安叔,您比较了解他。他那个十八平的心结,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能跟我说说吗?”
她提到十八平,安从显然有些意外,态度也谨慎起来,“你这么关心小川的事,是纯粹好奇想听八卦呢?还是有别的事?”
“我来他们球队,是为了给公司选一个有潜力的代言人。”梁友安说,“我知道,他的成绩在队里不是最好的。可是我老觉着——他会有机会的,您说呢?安叔。”
安从想了一会儿,“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我慢慢给你讲吧。”
“川儿他妈叫……童鹿,”坐下之后,安从斟酌了很久,才终于开口,“以前也是个羽毛球运动员,技术特别好。后来跟她同队的一个男队员谈恋爱,意外怀孕,就生下了川儿。生完孩子之后,这竞技状态一直没恢复上来,就退役了。人退了,心没退,所以就把得冠军的梦想、希望,全押在川儿身上了。”
“我当时是队里的穿线师,一直就特喜欢童鹿。我也知道,后来……童鹿嫁给我,多少有些无奈的因素。但我无所谓啊,谁叫我遇到了这辈子绕不过去的人呢。”
梁友安问,“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安从叹了口气,“十五岁那年,川儿打一场特重要的比赛,决胜局,十八比十八。川儿呢,就回头往看台上找他妈,那时候人就已经不在了。我估摸着就是那会儿落下的创伤。”
“她走得这么彻底?再也没回来吗?”
安从的记忆便又回到了变故发生的那个下午。
那天童鹿陪宋三川去比赛。他处理完队上的临时任务,正准备赶去体育场陪她一起看比赛,就发现了桌子上的信。
——童鹿写给他的告别信。